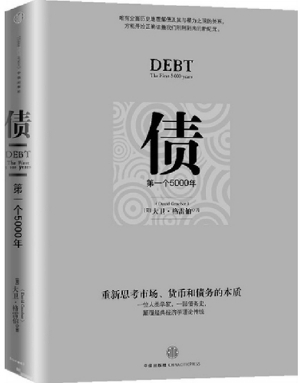|
⊙徐 瑾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债务环绕的世界,无论欠别人的还是被别人欠,甚至不仅仅是个人和私立机构,国家也往往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淖。若问债务从何而来,欠债还钱何时开始成为人类交往的共识?经济学家或许会从想象一个鲁滨逊小岛来论证,而人类学家会直接找到某个南太平或什么角落的小岛开始论证,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债》中的描述。格雷伯这本书涵盖了人类五千年以来的债务史,梳理了债务在形形色色国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他的不少观察对传统的经济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
例如,经济学家对货币功能的定义通常有三种: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手段,而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交易媒介定义为货币最重要的功能,甚至经济学家讲述货币故事时,绝大多数以幻想的以物易物世界作为开头。但是,人类在经济学之前已有交换、债务以及货币,因此,格雷伯批判上述观点完全是人为想象出来的,他以人类学家的敏感质问:“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怎么会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开办一家杂货店?他如何进货?如何安排这个幻想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点:我们在讨论穴居人、太平洋岛民,还是美国的边疆居民?”
更近一步,他的研究从巴西的南比克瓦拉人开始,村民还保留了简单社会的诸多状态,直到此时那里的人并没有以物易物,那么他们如何交换?“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件物品,他会大声称赞这件物品是多么好。如果一个人看重自己的物品,希望用它来交换更多的物品,他并不会说这件物品多么有价值,而是会说它没什么好的,以此表明他想保留它”。双方会讨价还价,甚至愤怒,但最终往往达成一致,彼此他们会从对方的手中把物品抢走。
这揭示了什么?经济学关于交换源于自利的论点并不符合现实。格雷伯引用了剑桥大学卡罗琳·汉弗里的研究结论, “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不要小看这一结论,这事实上揭示了一个很容易忽视的要点:人们并不易货,而是互相馈赠,有时以进贡的形式,有时会在晚些时候得到回赠,有时则是纯粹的礼物;在熟人环境中媒介是信用,而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也可以归结于欠条。
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对于原始交换与馈赠的研究痕迹,但格雷伯的并不满足于对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更在于对于当下的否认。作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他可谓正正经经的左派,也正因此他希望通过证明“欠债还钱”在道德的破产,一力主张免除穷人的债务,甚至试图通过本书证明周期性免除债务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比如《圣经》中对“禧年”的描述,“对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 利未记25:8-12)。”
通过回溯历史,格雷伯拓展了经济学的狭隘想象力,重新定义了货币以及债务的本质。这是这本《债》最大的价值所在。格雷伯的左派立场大概会令不少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他对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连篇累牍批判,也让人想起《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录》中对于发达国家一心通过各种阴谋来使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的桥段。对比之下,哈佛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较能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贫穷不是由于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它更多的是与金融机构缺乏也就是与银行缺乏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存在。这是因为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贷网络,他们才可以逃脱高利贷的魔掌。”问题在于,弗格森的看法虽然得到业内认可,但对于金融危机之后公众的滔天愤怒,经济学家们甚至金融界精英,恐怕不能仅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一笑了之。放眼当下,金融全球化正在退潮,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的新思潮的正在重新回来,格雷伯们的言论只是开始,“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欠你一份生计”呼声需要得到正视以及回应。
按格雷伯的论证,大约五千年前,人类已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而不仅是物物交换来交易商品。信用体系的存在远远早于硬币和货币。货币的出现不是为了方便交易,而是埃及等古国或苏美尔的神职人员为更有效地收税或计算财富而创造出来的,同时也作为人类之间的关系(债务与义务)出现的。价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场随后由此应运而生,它们吞噬了人类社会原本拥有的温情脉脉。金钱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欠债还钱的常识腐蚀了人类彼此关爱的本性。
格雷伯认为,一旦我们理解了债务的社会起源,就会乐于在条件发生改变时重新协商债务问题,无论他是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还是整个国家的债务。据此,他为被债务环绕的世界开出了一剂“药方”:免除所有国际和消费者债务。“这会奏效,因为它不仅能打打消除人们切实的苦难,而且提醒人们,金钱并非妙不可言,还债不是道德的核心,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