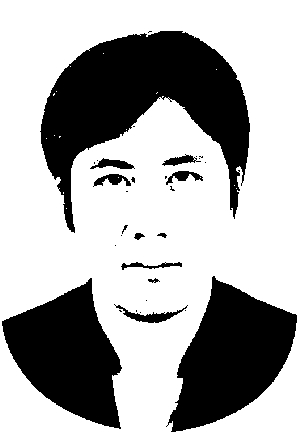|
周靖祥
中国近十余年的城市发展与人口总量、增量有密切联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也起了重要作用。在遭遇了拥堵、水污染和“雾霾”天气之后,超大城市发展问题又被归因为人口过多。30多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迅猛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增至2010年的2.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京、沪、穗等城市的常住居民中,约40%都是流动人口。
从本质上讲,我国大城市人口过密主要受制于两个制度性障碍:城市是行政区概念,一般都是行政驻扎地;城市通过非市场行政力量集中优势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和产业发展状况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城市行政级别。有研究建议中国面向2030年巨型区发展战略,优化和调整城市化区域格局。原因是我国中、东部平原地区正在形成十个巨型区,总体呈“个”字型展布。人口快速增长是巨型区的主要特征。2000年和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三个巨型区人口增长超过14%,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巨型区增长了18.4%,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增长了14.5%,广州-深圳则增长了22.5%。
针对城市移民的辩论,我们通常都把焦点放在应该“允许”那些情形发生,却忘了投注心力规划如何应对必然会发生的现象。限制或阻止移民,或仅限具备特殊技术的人口移入,绝对理性,然而,我们应该知道这些措施不可能长久。“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他们定居在那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亚里士多德对城市的定义今天仍然鲜活,如果把城市的生成和生长更多看成自然的过程,削足适履造成皮外皮内之伤,必然得不偿失。堵住“穷人”留住城市的移民歧视,法国这个移民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已有过前车之鉴。
在今日中国,土地城市化可以理解是个为模糊产权再界定和明晰化过程,人口城市化则是不同主体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力再分配过程。以人为本——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只是解决人口发展难题的单边行动,需要农村发展和城乡平衡进程合力,才能共推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然而在我们的固化思维形态里,总是认为“城市人口规模急速膨胀,城市病是不能承受的病痛”,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真实问题是人口空间分布失衡挑战并非是人口过度集中,反过来需要追问的是今天超大城市基础设施为谁建设。通常情况下,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识别指标,城市人口增长作为城市化速度的衡量指标。透过主要国家的变化趋势会发现,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数值就处于稳定状态,德国是典型例子,城市化人口增长波动加大;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速度方面,对应于日本、印度和中国,以法国为例,城市化水平稳定时期,城市人口增长也会加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轨迹变了,比较美国、法国、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化自然会发现,快速城市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总人口规模。
在城镇化上,中国体制运行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国家可大规模实验,依据自上而下的户籍和土地制度优越性,发展过程中两大制度的渐进改革被添置“倒逼”色彩,只有在足够的发展压力下才会启动改革。今天,中国城镇化又面临社会与经济联动才能疏导镶嵌其中的众多不确定性发展难题。对于超大城市,变“堵”为“疏”的城市化战略目标也就直接服务于“如何留得住人”。否则,超大城市必然要面对人口老化和人口逆流的特殊现实。追问人口老龄化归位到谁来养老?
无疑,我们的城市发展需要纠偏。政府主导城镇化大投资实为建成更多大城市、特大城市。而在超大城市危机管理机制建设中,建构预警防范机制设计,提高超大城市危机管理的预警监测能力是第一位。城市管理当局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城镇是大城市郊区化和腹地向外延伸的必然结果,而不能孤立于大城市发展。我国城市的规模如此巨大,改变如此迅速,忽视其面临的挑战是不明智的。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几点可操作性的建议:辨识城市政治与城市化政治,城市发展定位应视为有机体而非物理改变,不能视城市化为社会和政治运动,此其一;整合、集成城市人口数据库系统,以支持科学决策和动态管理调整,此其二;弄清楚“农转非居民的真实需要”,将移民群体作为城市成长的真正动力,此其三;从城市分治转向“共治”,采取超越经济发展认识社会建设的具体行动。此其四。
最后,笔者借用加拿大学者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的一段话,希望能激起更多人的反思: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和资源。另外,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作者系重庆交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