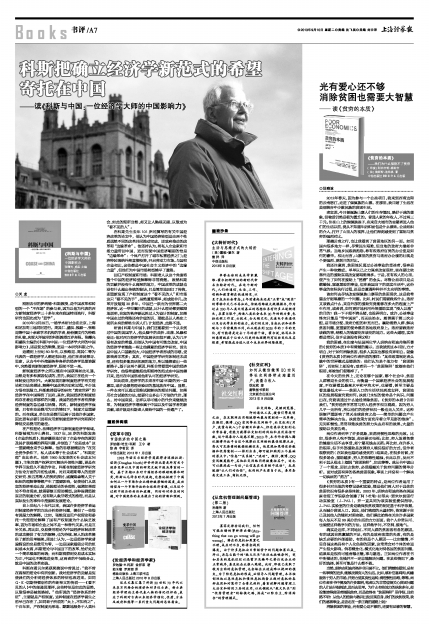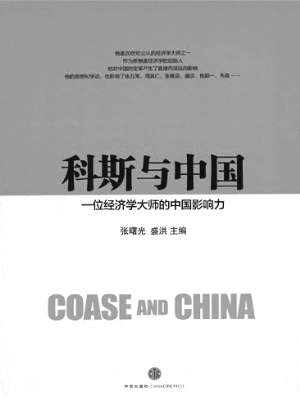寄托在中国
|
⊙天 龙
刚刚去世的罗纳德·科斯教授,是中国改革和转型的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因为以他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三十多年来在我国特别流行,科斯研究也因此成为“显学”。
2010年12月29日,一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上海和芝加哥三地同时进行。周其仁、盛洪、钱颖一、张维迎等中国十余家学术机构的学者,纷纷撰文作为特殊的礼物,庆贺大洋彼岸的科斯教授百岁寿辰。张曙光和盛洪主编的《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即是贺文的辑集,更是一本研究科斯之作。
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以张维迎、周其仁等为代表的一群经济学人都还很年轻,他们在苦苦探寻、思索,从古今中外挖掘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思想资源中,突然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眼前不觉一亮。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如此礼遇,当然是有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体制变迁的时代。大家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历史和过程,不少地方很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其次,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有探索经济制度的急迫感与热情。再次,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只有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才是重要的。而在我国,单位交易费用远高于其他许多国家,因此更有必要引进和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探讨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
在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科斯被视为开山鼻祖。1937年,26岁的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并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他的思想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科斯定理”由此命名。他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主张完善产权界定可解决外部性问题,更是在学界引发经久不息的争论。科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对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强调如果理论不符合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和发展理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许多经济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张维迎运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因为市场和企业之间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再比如,交易费用理论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持续、深入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周其仁认为,一边是经济学家普遍假设的交易费用为零,一边是国家超级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科斯理论与中国当下的改革,恰好处在一个简单框架的两端;而科斯观察到交易成本实际为正,中国也不断推进变革,这两者的中间结合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实践。
科斯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如同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的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如此的理所当然,却又让人熟视无睹,以致成为“看不见的人”。
在科斯先生去年101岁时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论文中,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即政府推动的改革和“边缘革命”。他坚持认为,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力量带回中国,进而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恰是“边缘革命”: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但他们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
回归产权制度和市场:科斯老人从这个角度将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解释得非常清楚。 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么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道理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中国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比什么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划经济,此路不通。
研读《科斯与中国》,我们还能看到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学人,他头脑中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很不满,认为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但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做一些让他满意的经济学研究。首先是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中国经济学者形成的思想,受影响者非常多;其次,中国经济学研究体制还未成型,还有很多能灵活拓展的地方,所以能探索出一些新路子。基于这两个原因,科斯非常看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他很希望能把他所期待的范式在中国传播开来,进而在中国形成他所认可的经济学研究。
如此说来,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科斯的另一层意思,或许是想把理论验证的基地放在中国。显然,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试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试验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万倍的代价。那么,对中国来说,怎样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来继续改革,为制度经济学增添属于中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新贡献,或许就是科斯老人留给中国的一份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