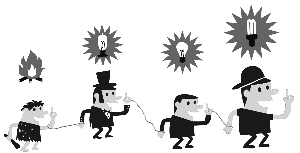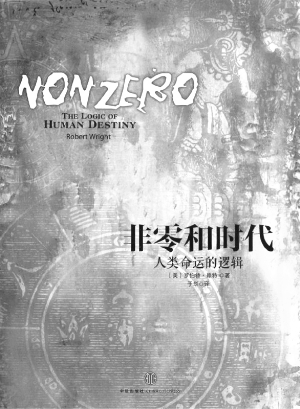| ||
|
——读《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
⊙胡艳丽
人类世界隐藏的万能驱动密码
当我们站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回望浩渺奔腾的自然进化及人类社会演进史,似乎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暗中指挥着生命的潮起潮落,人类社会的兴亡更迭。美国思想家,前总统克林顿的智囊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中,以随笔漫步的形式,展开了一场恢弘的探索旅程。作者一反从生物进化到社会进化的思维定式,直接由人类社会的分合演进起笔,用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反照地球生物的进化史,试图在各种生命形态的起承转合间探寻普世的发展规律。据他的概括,是非零和促进了生命进化和社会组织演进,非零和既是生物自利、利他的必然选择,亦是促进社会组织发育,增强社会适应性,实现联合生存的内生动力。
“非零和”的概念,对应的是零和,零和博弈是一种利益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对立,而非零和既可能实现正值总和即共同受益,亦可能出现负值总和即两败俱伤的局面。从大历史演进的宏观角度看,非零和互动产生的正值总和远远大于负值总和。作者因而乐观地判断,
伴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数不胜数的未来危机,人类将更加依赖群体性互动,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全球协作,形成一个日趋完善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超级聪明,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人类“智慧大脑”,向着全球治理层面“终极进化”。
关于战争,零和与非零和的思辨
最让中国读者心中一震的,当数赖特在书中对人类战争的深入思辨。表面看,战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是另一方的损失,胜利者书写历史,收获土地、掠夺财物,失败者付出财产、自由、尊严乃至生命的代价。而在赖特眼里,如果将视野放宽一点,战争呈现出的将是完全不同的样貌,绝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结局都是两败俱伤,摧毁的是几代人的家园,即使获胜方也必然要面对人员的伤亡和财力、物资损失,以及道德审判。因此,两方加总,任何战争,都是一场负值的“非零和”,没有人会成为战争的赢家,所有人都要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局面。
如果站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在百年之后再看这一段风烟浩荡的历史,战争又将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除了破坏效应以外,战争还将激发社会新一轮的发展活力,新的战胜者为维持统治,在经历最初的肃杀之后,必定摒除战败方的种种积弊,重新为社会制度定型,摧毁原有的利益集团和清理盘根错节的社会流毒。放下种族主义和家国意识不谈,放眼数千万年人类社会分合演进的历史,战争或说是战争的威胁居功至伟,它以表面上零和博弈的形式,促进了实质上非零和协作。
战争是人类社会各种竞技中最残酷的一种,它以“军备竞赛”的形式,激发了全社会物质工具的创新和人们合作形式的创新,演化出了分工渐趋精细、能够协调联动的社会有机组织,包括原始的族群、部落、城邦、国家。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战争促进了人类种族、文化、经济的大融合,整个人类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各种族不断融合,求同存异的历史。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旅途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跨越文化与语言的障碍
按作者的归结,人类社会文化产生差异的原因并非具体族群的基因或智商造成,而是因具体生存环境的不同,催生出不同的生产、生活、协作方式。面对不同的生存危机,人们衍生出不同的智慧,发明出各种实用工具,催生各种“非零和”协同方式,产生不同的文化,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便是因此而生。
为说明这个观点,作者深入分析了人类文化的活化石——美洲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美洲原住民因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尽管生活方式原始简单,但他们同样为生存而设计出了大量的非零和游戏,比如集体狩猎、守望相助,甚至“进化”出了资本投资与劳动分工的初级模式。衮山人和肖肖尼人生活方式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需要常年迁迁徙,文化没有落地生根的时间和空间。简言之,那些居无定所,游荡不定的民族,因彼此合作的机会较少,而导致他们的文化难以累积,以致发展迟滞;而生活相对稳定,人口密集的族群,他们因密集的接触和不断细化的分工而促进了集体性创新,而这种创新的技艺更容易在代系间流传,进而发育成相对成熟的文化体系。
人类从身体到智慧的全面“发育”,主要得益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互动。文化并非在个人的大脑中独立产生,而是依附于整体,因整体的需求而生,因整体的认同而不断传播、生长、进化。有用的创造,即使在世界的某一个角度被打压扼杀,也会择地重生,实用的技术,可以轻易跨越文化与语言的障碍,就如同生命之树一般,一根树枝被折断,总会在另一处冒出新芽。
信息化时代促进全球大脑的发育
文字的发明使人类拥有了除大脑外的第二记忆,开启了人类全新的非零和领域。文字不仅是记录、传播、交流智慧的工具,也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建立信用的中介,它使人类远距离精准传递信息从可能变为了现实。围绕文字的书写、传播,一系列的物质工具被发明,一批新型的社会机构被建立。而文字所有的功能,最终都可归结为它促进了人类社会非零和关系的进一步多样化,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沟通协作。文字的广泛应用,为建立更复杂的社会机构,形成相对完备的制度、为人们制定通行的规则提供了条件。
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合作走向全球化非零和时代。合作将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全球化的互联网络成了全球沟通合作的平台,国家、种族、政治的限制有了被架空的可能。任何的愚民之术,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封锁之术都将成为自欺欺人的游戏,这是一个全球智慧共同激荡的世界。全球化的非零和经济合作越多、越紧密,一触即发的战争便会越少;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的“非零和”最终促进的都将是人类“全球大脑”的发育,一个联合思考的世界正在形成。此时虽然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充斥着纷争和不信任,各种摩擦时常上演,但面对人类未来的共同利益,由全球化协作向全球化治理迈进,需要的也仅仅是时间、机遇,以及我们打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勇气和行动。
本书的探讨别开生面,作者“邀请”了多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先哲,包括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哈耶克、康德、卢梭等人共同为这一场正反合的大辩论、大碰撞助威,书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要想在众多思想精英的掩护之下,找到作者的思想原形,理出作者明确的思路、观点,需要颇费些心思。
当然,在社会科学文化领域,从来没有绝对正确的观点,一切都在时光推进中被不断质疑、修正、丰富、完善,作者的这些观点也是如此,这同样是一种“非零和”,促进“社会大脑”发育的思辨过程。正因为有“非零和”的思维碰撞,人类的思想才能渐趋理性、成熟,对未来才能有更深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