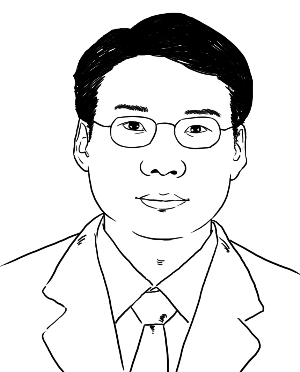|
达到一种极致时,反而显出一种相反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离极致还远着呢。人也不能老想着一定要达到极致,那是一种极端心理。尽管很刺激很决绝,甚至很蛊惑人心,却限定了自己的视野和立足之地,终将不可持续。
□袁 东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无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经意不经意间的这一缕缕稔熟之语,如满天和风,飘逸之中袅袅升冉,拂过千秋万代。
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朴槿惠自传》中说到她时常送给外国宾客的一种礼物“戒盈杯”。这是一位制作陶器的朋友向她推荐的酒杯。设计这种杯子时,在一定位置上打洞,酒倒的适量就不会流掉,如超出七成,酒就会流出。这可真是“大盈若冲”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亦在提醒人们“凡是不可过满”。
达到一种极致时,反而显出一种相反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离极致还远着呢。人也不能老想着一定要达到极致,那是一种极端心理。如果极端,尽管很刺激很决绝,甚至很蛊惑人心,却限定了自己的视野和立足之地,终将不可持续。在这一意义上,孔子的“中庸”与老子的上述劝诫有着相同效果。
这使我想起了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塑造的两个典型人物,及其所要表达的理念观点。小说中的巴扎罗夫,一位医学专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是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代表。他年轻而活力十足,坚强沉着也自信,注重实际行动而专心于科学实验。但他不相信任何准则,只相信感觉,一切取决于感觉。不仅不尊重任何传统,反而对现有一切予以全面无情的否定。不相信历史逻辑。他的额头上永远贴着“否定一切”的标签,他没有建设,只有满心思的“将地面打扫干净”,因而是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扎罗夫不但绝对瞧不上贵族,也取笑仆人农民等下层人士,反感文学艺术,对所谓的美异常冷淡。
帕维尔是另一个典型人物。这是位开明、进步的贵族,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他原先一直在彼得堡的贵族圈里,因与一位贵夫人坠入爱河而深受其伤,被邀请回到弟弟的农庄里居住一段时间。尽管在乡村,帕维尔仍然衣着得体,举止优雅,书房古朴而讲究,谈吐不俗。他的起居基本上是英国式的,平常在公共场合冷漠而寡言。即使偶尔说上几句,也是英国自由主义的理念与表述,他也不主动取悦年轻一代。他对现实并不满意,希望变革,但他信奉准则,讲求信仰,尊重传统中好的方面,主张首先肯定“文明果实”,然后才是否定,建设为重。其实,帕维尔有着铁一样的坚,冰一样的冷,不仅不是浪漫主义者,反而有着那么“一点儿法国厌世主义”,并不善于幻想。但是,他肯定文学艺术,也不排斥浪漫主义情怀。
在屠格涅夫的笔下,这两位典型人物终于相遇了。不用说,一相遇就是激烈的冲突。
在帕维尔看来,巴扎罗夫狂妄放肆,目空一切,没有一丁点儿敬畏,态度傲慢粗暴,说话有气无力,对什么都心不在焉。巴扎罗夫则反感甚至仇视帕维尔的一切,无论是他的贵族仪容,还是他的拿腔拿调,更讨厌他时不时夹杂一两句英语、法语或德语所表达的观点。不管帕维尔如何雄辩阔论,巴扎罗夫一律视其为“没有出息”和“无所事事”的什么也没用的空谈。
在不多的几次交锋中,被激怒或感到受凌辱的,多半不是巴扎罗夫,而是帕维尔。无论帕维尔如何扬起雄辩的旗帜,鼓满各种准则信仰的风帆,巴扎罗夫都总是懒散而傲慢地用一两句话就给顶回去了,他那无所谓的态度和没有底线的虚无主义,越发令对手恼怒。然而,越是恼怒,帕维尔越是拿对手没有任何办法,不仅说服不了人家,反而使自己破绽百出。这就好像一个轮胎,总以为充气越满就越是坚硬,越能碾压一切,殊不知,越是气满,越容易被一小根细钉扎破,成为废物一堆。
结果呢?那位不注重骑士感情更不用说柏拉图式恋爱,只注重女性“窈窕身段”和交往愉悦,反对一切贵族的巴扎罗夫,恰恰真心实意而又执着地爱上了美艳聪慧的贵族妇女奥金佐娃,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他因爱情失败而变得更加怀疑悲观,带着未遂之志遗憾地离开了人世。巴扎罗夫没想到正是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亲手将他的理论毁掉,他竭尽所能抑制天性而克制自己浪漫倾向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
那位贵族自由主义者帕维尔最终离开了俄国乡村,隐居到了德国的德累斯顿,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开明、进步的贵族气派。不过,他也没有躲过爱的激情的撞击,终究“孑然一身,渐入黄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将至、青春不再的岁月。”陷入了“无目的生活”的“可怕空虚”之中。
掩卷深思,这两个极端的人物,都是悲剧性人物。相比之下,巴扎罗夫更加极端,但他并没有因为极端更具穿透力而成功。而观察一下现实,俄罗斯这一百多年来似乎走了巴扎罗夫式的道路,与之相伴的,从内战、集权、高度计划控制再到最终苏联解体,无不是一幕幕极端式痛苦。自上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就一直处在回归“大盈若冲”的中庸之路上,但是,这一回归处处显示着莫名的艰辛,迄今也没有完全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智慧就是智慧。智慧不是知识。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只能启迪。智慧的形成包含了历史的沉淀,其中既有痛苦也有幸福;智慧的启迪,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轻易领悟到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