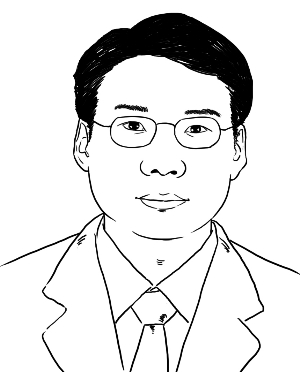与林肯的隐痛
|
□袁 东
人类的创造与文明,离不开想象力,既需田园想象力,也需要道德想象力,更需要两种想象力在现实节制基础上的结合。人应当努力在现实与想象之中找到各自的均衡点。
想象力是创造的基础源泉,是生命力的首要体现。尽管想象被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区别于幻想,但即便是幻想,也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忽视这一点,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就会发生偏离。
哲学家可将幻想、想象、意志与认识,做出一系列定义与区分。但人类世界总是处于真实与想象之间,完整而真实的世界与人类总保持一段距离。人所面临的,总是外在与内在的不同组合。正因如此,那位大哲学家叔本华,干脆将他那本代表作取名为《作为意志表象的世界》。
想象,可以是田园想象,也可以是道德想象。区别只是能否有所节制,亦即有无来自现实的规约。想象如同飘向高空的风筝,总有一条线连在地面,被那只握线的手牵引。没有了线的风筝,已不再是风筝。那只握线的手就是现实,离开现实节制与规约的想象,正如离了线的风筝,已不再是想象,至少不再是对人有益的想象。
富于田园想象的中国文人墨客与典籍不胜枚举,而对近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西方的卢梭。卢梭总在迁徙之中离群索居,一心向往隐于田园,却又得不到宁静。窘迫与烦躁,又加重了他的田园想象与游离。卢梭的想象没有节制,不受任何现实的规约。他由厌恶现实到一味地逃避,可又无法完全逃离。这反而更助长了他的田园想象癖好。他的浪漫想象透出的是肆恣挥发,甚至是放纵。他所谓的“自然生活”,几乎是对人类“初始状态”或“过往”的纯粹田园想象。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开篇就承认:他对“过去”所做的勘察“不应被视作历史事实,而只应作为假定的、有条件的推理来加以对待。”
他勾画的“新社会”,只是他在一堆“假定”和“条件”下的推理结果。而这些“假定”和“条件”仅仅是他不加节制的想象,对现实社会厌恶甚至仇视的投射:周围的一切现实都是“恶”,只有他连同他的想象才是“善”。多么尖锐的对立,又是多么的自以为是!
问题是,任何田园想象都有巨大的诱惑力,何况卢梭那种渗透着敏感和激情的文字,更使他想象出的那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对底层大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不受历史与现实节制的浪漫作家一旦成为社会注目甚至跟随的核心,非理性的狂热就会像山洪一样爆发。“推倒一切重来”的狂妄激情,足以将周围的一切吞噬,最后连他自己也被吞没。每个人都将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怨恨和愤怒,归于了外在社会:“恶”是外在的,唯独自己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纯洁无瑕无辜,自己是善的。这恰恰是内心不受任何约束与规训,无所顾忌的肆意放纵的张狂,驱使人类走向了非理性。
卢梭的田园想象偏执地放弃了人的内心禁忌与建设,消解了应有的敬畏与谦卑,这与林肯的道德想象恰恰形成了比照。
当初在那个破败的小小律师事务里的年轻林肯,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不仅企望得到国会议员和总统的位子,更想做出一番小于华盛顿的大事。只不过,他把这种野心与抱负隐藏得很好很巧妙而已。林肯果真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废除了区域性奴隶制,成了美国历史上与华盛顿比肩的伟人,但长达近5年的内战致使近60万人失去生命。他深知这场战争有着重大的社会和生命体代价,为此深陷痛苦纠缠之中。
就在遇刺的那一周,林肯视察完弗吉尼亚州的军队指挥总部,在回华盛顿的“河流皇后号”轮船上,向随行人员大声朗读《麦克白》数小时,重复了两遍下面的话:“顿肯在坟里了;/经过人生的疟疾,他睡得很好。/叛逆已经做绝了,刀也罢,药也罢,/内忧外患也罢,再也没有什么/能伤一根毫毛了。”他将这种内心的清醒意识和痛苦,巧妙而委婉地通过他喜欢的《麦克白》的台词表现出来。
可见,林肯有野心,但也有原则,无论他的野心与原则,还是其矛盾与痛苦,都显示了他那种现实规约中的道德想象力。林肯尽管只是间接地愿意暴露自身性格中的阴暗深处和秘密之所,愿意探明潜伏其身的“幽黑欲望”,而这正是他道德想象力之强、心灵之伟大的明证。
如果说林肯既整顿外在世界又检视内在世界,那么,卢梭就只是抱怨仇视以致推翻外在世界而放纵内在世界,任其恣意驰骋无限扩张,认为内心永远而绝对正确。只是,过了头的田园想象已成了负面的道德想象,这同样有害。如果认为人性非恶即善,这本身就是在走极端,在不受现实规约。关键是要有所节制。还是培根说得好:“很少有人不是在善恶艺术的混合体中被培养大的。”
人类的创造与文明,离不开想象力,既需田园想象力,也需要道德想象力,更需要两种想象力在现实节制基础上的结合。人应当努力在现实与想象之中找到各自的均衡点。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