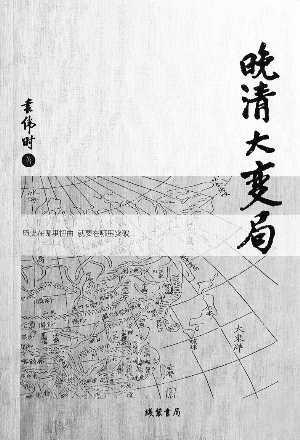遮蔽了的历史细节
|
——读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胡飞雪
英人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当然极有道理,但也切不可绝对、僵化地理解。如果读的是庸人或是低眉噤声的奴才捣鼓出来的史书,只能使人越读越糊涂;如果读的是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严谨之士写出来的史书,才有可能越读越明白。笔者以为,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就具备了后者的诸多元素,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读者“明智”:
一是通过中外比较,通过展示中外的不同、差异、差距来描述、解释晚清宗法专制社会情形。如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着重讲了西欧社会之自治,以对照同时期中国宗法专制。自治,包括城市自治和行业自治,是中世纪西欧的普遍现象,《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之特许状》重申了城市居民的自由、自治的权利,强调保障财产权;神圣罗马帝国于1368年12月也推出了《奥格斯堡第二次行会文告》,保障自治,而这一年正是朱元璋开始做皇帝的时间,中国的宗法专制政治进入巅峰阶段。清承明制,这就不难理解,直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当立宪改革千呼万唤之际,清朝竟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推出一个皇族内阁,大有将专制统治进行到底的架势。书中这种把在同一时期里发生在中外的不同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事例很多,如引在华美国人林乐知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之言曰:“东方诸国,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迟,莫如中国;改化之难,则莫如印度。”一人或一国之特性本质,是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诚哉斯言!
二是通过对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研究,全面提升国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袁先生指出,晚清有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第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它涉及的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林则徐是典型人物。第二类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立意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主义志士的代表,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魏源等人也是。
林、郭这两类爱国者的首要差别,表现在如何认识、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在19世纪,西方列强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要捍卫独立就要以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任何身处其境的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林则徐的爱国主义表现之所以具有近代(落后)的因素,盖因他仍处于很不自觉的状态。在林氏遗文和日常言说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即使在晚年退仕闲居在家时,林还明里暗里鼓动地方绅商士民进行反洋人入城运动,拒绝洋夷商民进入福州。而郭嵩焘在出使英国前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国之内政外交实为一而二、二而一,是一体两面,处理好内部事务,方能处理好涉外事务,处理不好内部事务,适足以招致外部祸患。
比较林、郭两类人之爱国观,我们在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爱国,远远不是简单的对外示硬逞强,认识、承认中外差异、差距,以普世价值为参照系,见贤思齐,反求诸己,内修政教,外求平等,才能赢得普世尊重,这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尊重的爱国主义。真正自觉性高的爱国者必然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郭嵩焘的眼光比同时代人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郭嵩焘的思想高度,即使到了今天,超越者仍凤毛麟角。
三是通过对关键人物的研究,总结历史演变进程的成败得失。比如他写魏源,指出魏源的“高明之处”:一是“倡导破华夷之辨,立各国平等相处的观念”;二是为以谋利为耻的名教限定了适用范围,为庶民逐利确定了根据。魏源倡言官员不可逐利,更不能与民争利。而百姓则可拒绝名教的束缚,以利为行动导向。魏源此言堪称石破天惊。再如徐继畲,曾长期被戴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理由是他在福建巡抚任上时允许英人租住福州神光寺。在作者看来,徐是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正能量,因为他的《瀛环志略》“帮助中国人民正确了解西方”。本书还写到洪秀全、洪仁玕,指出洪秀全不过与历代同类一样,也在做着“胡越贡朝,蛮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的帝王迷梦美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是结合实际学习西方的佳作,但其价值仅限于思想史,并无探索实践的必要条件和环境土壤。
再看袁先生对王韬、冯桂芬、郑观应几位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析。王韬有言:“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王韬学西法之具体学法尚可讨论,但其方向无疑是对的。冯桂芬提出“鉴诸国”与“一于和”是处理与西法列强的关系必须坚持的原则。郑观应则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认为这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显然,这比某些洋务派只片面学西法坚船利炮向前进了一步。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博弈,洋务派只知军备,甲午战败实属必然。甲午战前,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曾对严复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苟于海军,未见其益也。”满族亲贵文祥任军机大臣17年,临死之际上疏密陈大计:“说者谓各国性近羊犬,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他因此建议重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他把这么重要的话留待将死之时才说出,多么可悲可叹!
本书最值得今人参看的章节之一,笔者以为是“埋葬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那一章,内有袁先生对国民党革命叙事的辨剖:“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掌权执政后)的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编造的‘十次革命’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史话,是为确立它的‘正统’地位服务的,不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组织、领导的反清武力行动都被排除在外(例如,1900年自立军事件就规模和影响而言,远远超过革命派的多数‘革命’)其他推动民国诞生的活动更被抹杀,如此猵狭,不足为训。”
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运行,而是曲线螺旋式运行。所以,历史常常呈现前进和倒退共存的状态。历史呼唤巨人,可登上时代舞台的却常常是侏儒。历史该破浪前行,掌舵者却常常踟蹰不前。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覆舟犹能避免,舟自沉却不可救药。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前人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不可不察。这就是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今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