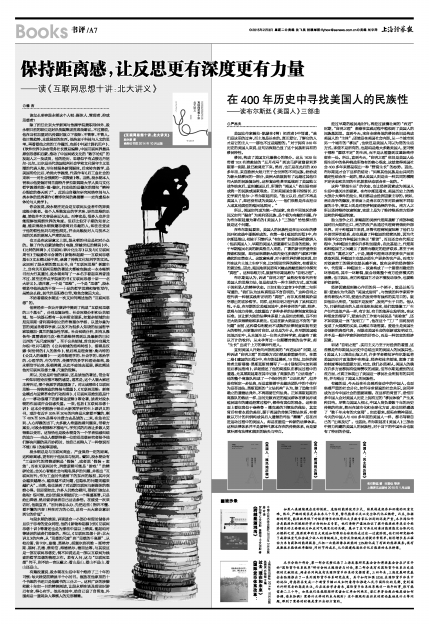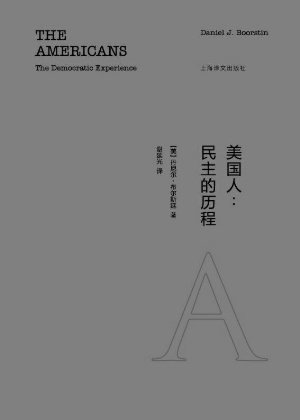| ||
| ||
|
——读布尔斯廷《美国人》三部曲
⊙严杰夫
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在《啊!拓荒者》中写道,“我们是这里的过客,而土地是长在的。真正爱它、了解它的人才是它的主人——那也不过是短暂的。”对于拥有240年历史的美国人来说,这句话深刻凸显了这个民族所具有的移民特性。
移民,构成了美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这从1620年带着102名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到达马萨诸塞普利茅斯那一刻起,就已被奠定下来。然而,也正是在此后的200多年里,来自欧洲大陆乃至于全世界的不同民族,纷纷成为新大陆移民的一部分,美洲大陆就拥有了远超过其他任何大陆的民族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甚至延续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直到建国以后,所谓的“美国人”依旧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或国家观念。正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所说,“独立以后,他们不再是英国人了,却还没有成为美国人……他们依然是弗吉尼亚人或其他类型的殖民地居民 。”
所以,美国如何成为统一的国家,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又如何“融合”为美利坚民族,是个极为有趣的问题。作为布尔斯廷最为著名的《美国人》“三部曲”恰恰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布尔斯廷看来,美国人的民族性是在近400年的移民开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第一卷《殖民的历程》中,布尔斯廷指出,相较于习惯听从“有知者”阶级指导的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早期的美国人更愿意听从自身的经验。对于早期殖民北美的新英格兰人来说,广袤的新世界亟待去探索和发掘,却还面临着新大陆内变化多端的气候和不断袭扰的印第安人。这就意味着,对于新世界的移民来说,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比对理论世界的探究,有着更大的紧迫性。因此,殖民地居民更有兴趣去推敲经验而非探究“真理”。这种思维方式,就被布尔斯廷称为“自明之理”。
布尔斯廷认为,诉诸“自明之理”虽然没有取代所有美国人的思维方法,但是却成为一种主导的方式,成为属于美利坚人的精神状态。正如《独立宣言》中的第二句所写道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自明之理代表一种被实践所证明的“真理”,而非某些精英阶层空想出的玄妙哲学。同样,这种自明之理代表了某种实用性。于是,在早期的北美殖民地中,多种多样的气候、经济、景观与地方传统,也就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法律制度和职业标准。这让新大陆的法律体系看上去是如此粗糙,远不如旧大陆来得精细和系统化。但是在新大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面前,这种看似粗糙而不成熟的法律制度却拥有更大的弹性,而更能应对自如。这也是为什么,在早期美国殖民地历史中,从未诞生过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却遍布了数以万计的牧师;从未孕育过一位颠覆传统的法学家,却“生长”出成千上万的律师代理人。
直到美国人开始向西部拓展的“西进运动”时期,这种诉诸“自明之理”的思维方式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二卷《建国的历程》中,布尔斯廷提到,19世纪,加州的探险者兰斯福德·黑斯廷斯曾撰写了一本《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民指南》,详细描述了他的商旅队在移民过程中的遭遇。尤其黑斯廷斯在其中记录了商旅队的“立法观念”:他的整个商旅队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立法机构”,但并没有制定一步法典,而是直接着手去裁决团队中的个体行为是否违法。黑斯廷斯的“立法机构”认为,除了造物主所确立的道德法典外,不再需要任何法典。正如黑斯廷斯的商旅队的做法一样,当时无数西进的殖民群体在移民亦或殖民城市的建造经营过程中,都带有类似的观念。这种表面上看似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法的做法,其实背后有着本质的差别,源于英国的传统习惯法体系,有着数以万计的判例构成供后人遵循的司法“藩篱”,但在西进运动过程中的美国人,却是在塑造一种新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并不是要替代原本存在的传统体系,而是要填补原有法律和规则的缺失与空白。
经过早期的殖民地时代,再经过波澜壮阔的“西进”时期,“自明之理”渐渐在实践过程中植根到了美国人的民族基因里。直到今天,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依旧是构成美国人的“主体”;即使是在美国社会内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移民”,也依旧是美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即使不是所有的,也起码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更习惯于那种“漂浮不定”的生活,而不是从摇篮到坟墓始终停留在一处。所以,直到今天,“自明之理”依旧是美国人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所抱有的核心观念,这就使得美国社会400多年来都呈现出一种“野蛮生长”的态势。因此,布尔斯廷才会下这样的结论:“如果其他民族是由共同的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的,那么美国人则是由一种共同的模糊不定状态和共同的生机勃勃状态联合在一起的。”
这种“野蛮生长”的状态,也让经济因素成为美国人生活中最关注的要素。在布尔斯廷看来,美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大事件的发生,背后都是由经济因素主导的。例如,南北战争的爆发,在表面上是南北双方在对奴隶制不同态度的斗争,事实上则是对经济制度选择的争执。南方人之所以坚持维持奴隶制度,实质上是为了维持维系南方经济运转的种植园制度。
独立战争之后,新崛起的美洲代理商垄断了南部种植园对旧大陆的出口,南方的农产品通过代理商销售到外部世界。对于种植园主来说,尽管代理商制度阻断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却也规避了种植园的经营风险,因为代理商不仅会向种植园主购买“期货”,而且还会在代理过程中,为种植园主提供许多附加服务。在此基础上,代理商和种植园主之间建立了紧密而稳定的经济联系,甚至于两者成为“莫逆之交”。于是,随着代理商寻求更多农产品来获取利润,种植园主也就必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而南方对奴隶劳工的需求也就长盛不衰。就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代理商-种植园主-奴隶构成了一个紧密而稳定的环形结构,其中一环断裂,就会导致整个南方经济模式的崩溃。也正因此,南方种植园主才会不惜发动战争,也要维护奴隶制。
经济因素起到核心作用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以托马斯·爱迪生为代表的“美国式发明”。与传统的科学家和学者有着很大不同,爱迪生的发明带有强烈的实用目的。就如他自己所说,“发现不是发明”,发明产生于目的。他认为,只要把适当的人适当地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像工厂生产任何其他产品一样,有计划、有目的地弄出发明来。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爱迪生的工作室与其说是“实验室”,还不如说就是一座“发明工厂”,他在这个“工厂”里将发明变成了大规模的买卖,以满足市场需要。爱迪生是美国社会创新的典型代表,而驱动美国社会的创新或发明动力,并不是一般科学家所拥有的好奇心,而是一种切实的经济因素。
诉诸“自明之理”、实用主义乃至于对经济的看重,这些都是布尔斯廷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美国人的民族共性。《美国人》三部曲出版之后,许多学者都批评布尔斯廷将美国历史片面地集中在商业、经济和技术领域,忽略了政治制度等其他重要方面。对此,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人的确在许多方面都拥有值得赞叹的成就,但布尔斯廷提到的这些方面,才真正体现出了美国这一移民社会所拥有的共同性,并勾勒出了美国人的民族性。
有趣的是,今天处在社会剧烈变动中的中国人,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分化,如何寻求普遍的社会共识,这同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恐怕许多中国人会对美国人历史上拥有过的“移民体验”产生某种共鸣。尽管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背负着数千年的历史传统的约束,然而在城市化和全球化方面,却也同样遭遇了 “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此看来,起码在精神层面,今天的中国人与400多年前的美国人一样,都书写着自己的“出埃及记”。也因此,布尔斯廷在《美国人》三部曲中努力构建的美国人的民族性,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也就有了特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