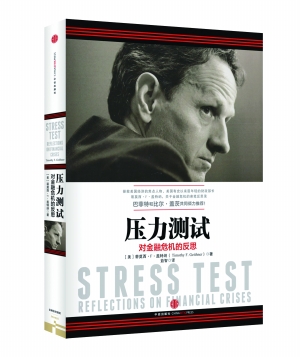被逼成“拆弹”专家
|
⊙益 智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使众多金融大佬和企业巨子走下神坛,也成就了一批业余财经畅销书作家:曾经的财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当然也包括本书作者盖特纳。卸任一年后,他现在已是著名私募基金——华平基金董事长了。
盖特纳在2009年1月就任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时不到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长,而在此之前,2003年他就担任了纽约联储行长,1999年即担任过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盖特纳小时候的学习生活可用颠沛流离来概括,他从小随在福特基金会任职的父亲周游世界,曾在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和津巴布韦生活过,学过汉语和日语,从曼谷一所高中毕业,考上美国常春藤联盟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念了研究生。盖特纳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与达特茅斯学院关系不小,他的前任保尔森就从这所学院本科毕业,当时是常春藤东部联盟明星橄榄球达特茅斯校队的内边锋,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中总是把小师弟盖特纳称为“我值得信赖的朋友”,可以想象,盖特纳被奥巴马提名为财政部长候选人遭到强烈反对时,保尔森的支持多么有力。
在美国政坛和商界,“圈子”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得强大。保尔森妻子温迪是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的,这家学院其实就是只招女生的麻省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有学术联合关系,如学生参加5年双校课程项目,毕业后将获韦尔斯利和麻省理工学院双重学位。巧合的是,温迪是希拉里·克林顿同班同学兼闺蜜,在学生活动中关系密切:温迪是班长,希拉里是学生会主席,当2000年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时,温迪在纽约为她主办了最早的募捐活动。希拉里虽然竞选总统输给了奥巴马,但还是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盖特纳在书中记述了他2013年卸任财政部长时同事为了送别排演的一场情景剧:“这场戏剧的结尾是,2017年1月21日,希拉里·克林顿——好吧,也是由财政部职员饰演——在总统办公室里,说她需要我在财政部再待上6个月,或是一年。”谁能否认当盖特纳被提名财政部长,遭到偷税指控等炮轰时,女强人、前总统夫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没有助一臂之力呢?
除了奥巴马,盖特纳提到最多的重要人物是劳伦斯·萨默斯。萨出生在犹太家庭,父母都是经济学者,他的叔叔保罗·安·萨缪尔森和舅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默斯是神童,16岁就进入麻省理工,28岁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后来还当过颇具争议的哈佛大学校长。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萨默斯担任奥巴马竞选班子经济顾问,奥巴马当选后提名他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曾是盖特纳的领导,也是盖特纳财政部长位置强有力的竞争者。
盖特纳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也非常有趣,这事发生在奥巴马准备提名他当财长前的尽职调查时,“参议员奥巴马随后询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背景的问题,所以我描述了我在印度和泰国的童年轨迹。我们讨论到了一个奇怪的家族巧合:当我父亲在运作福特基金会亚洲区项目时,基金会为参议员奥巴马已故的母亲安·邓纳姆提供了资助,那时她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看来圈子不仅存在于平行的空间,也潜伏在历史的时间长河。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共事需要圈子”的威力,校友圈、夫妻闺蜜圈、家族圈,当然在多种族的美国,千万不能忘记族裔圈,而盖特纳正好也是犹太人。2008年,名为尤里·奥纳里的好事者做了个统计,当时美联储的联邦储备理事会所有最高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伯南克都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只构成美国人口的大约2%。在12名地方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有9名犹太人,占75%,当时盖特纳是纽约联储行长,耶伦是旧金山联储行长。
美国社会是1%的精英带领着99%的平民,有了几百万的精英人群,整个美国就可以称霸世界。看看盖特纳的朋友圈,的确如此。
可是,为什么在云集了顶尖聪明人的精英团体领导下,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译者认为,人类发展除了需要聪明智慧,还需要道德。华尔街集聚了精英中的精英,但2008年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的形势,激发了一些精英的发财梦,他们居然设计出不考虑还款能力且没有首付的住房按揭产品,并将之证券化卖给全球投资者。因为他们是精英,所以99%的美国老百姓都相信,踊跃购买金融产品,并且通过羊群效应传染给了全球投资者。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在这些“金融创新”幌子下大发横财,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背景的住房金融机构乐享其成,美国国际集团居然还敢为这些违背金融规律的业务活动提供保险背书,高盛、花旗、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头既煽风点火又隔岸观火。一旦房价走势逆转,按揭客户违约,华尔街精英们设计的产品漏洞暴露后,沙滩上的多米诺骨牌就开始坍塌,自贝尔斯登破产后,前后两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盖特纳便陷入了救助与道德风险的两难境地。
危机之初,监管层很自然倾向于让市场去教训这些坏小子和纵火犯,于是就有了百年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该公司老板福尔德因之前的业务风生水起而有了骄娇二气,而当时的财长保尔森原本是高盛老板,两人以前是竞争对手,所以保尔森顺水推舟不救助,曾经神气活现的福尔德在健身房被原来的手下员工痛扁了一顿。而让保尔森、伯南克始料不及的是,雷曼兄弟破产导致银行挤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貌似大而不会倒的金融公司都岌岌可危,平日趾高气扬、道貌岸然的银行家惶惶不可终日,这也让公务员出身的盖特纳感到很解气,不过保尔森可是投行出身,马上意识到经济已处于峭壁边缘,不可继续快意恩仇,必须暂时搁置精英内部矛盾,实施大规模救助,防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
在这个背景下接过财政部权杖的盖特纳,立志成为“拆弹”专家。对于救助纵火犯与道德风险的关系,他态度明确:“人民憎恶政府紧急救助那些愚蠢的金融巨兽,但是如果他们的债权人或者整个市场失去对他们履行义务的信心,全球范围的金融系统就会彻底崩溃,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秉承这个理念,盖特纳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他与各方反对救助华尔街力量的抗争,也因此任职财长期间经常受到非议,人们说他和华尔街金融巨头走得太近,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含蓄地说他与市场太近。所以盖特纳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辩护和解释他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决策。贯穿着这本书的线索之一就是压倒性力量的金融救助,以及由此造成的道德风险之间的矛盾。盖特纳就像美国队长,遇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压力,排除了党派斗争的压力,强行推进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坚信亡羊补牢不如治未病的理念,虽然当时的行为似乎南辕北辙,但结果却很棒:盖特纳被提名财长时,金融危机正在肆虐,美国经济正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崩溃,GDP下滑速度达9%。他上任那一天,标准普尔指数收于836.59 点,距2007年的高点骤降了47%。而就在我译完本书时,美国股市迭创历史新高,标准普尔指数较当时翻了一番还不止。美联储不仅还清了纳税人当时救助支出的钱,还大赚了一笔。
前面提到圈子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提到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党派圈,从盖特纳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我感到党派争斗其实都是幌子,真正起作用还是各团体圈子的核心利益,而这些圈子里的密友可以使不同党派人士亲密无间。盖特纳年轻时曾加入共和党,后来脱党,他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身份入阁奥巴马政府的。保尔森的母亲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但1995 年后,她转而支持民主党,痛恨伊拉克战争,尤其反对小布什,而这并不影响保尔森入阁布什政府。2001年,原本是民主党人的布隆伯格,却以共和党人身份成功竞选纽约市长。他“叛党”的原因很简单,民主党推举候选人的程序太过复杂;如是共和党候选人,他胜出的概率更大。更为搞笑的是,他于2007年6月突然宣布,已不再属于共和党阵营,而将成为独立派人士。
从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我觉得最值得汲取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对待非常规的金融经济形势,需要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以强大的决心去贯彻,而不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本文系《压力测试》译者为本书所写的序,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