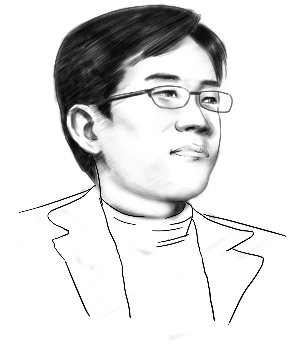历史文化基因
|
■斜阳芳草
在诸多关于温州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温州人善于抱团合作。温州人通过宗族、结盟、宗教等渠道形成的强连带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出于“表意型”的需要,它更多承担了“工具型”的社会功能。温州民营企业如此兴盛,绝不是偶然的。
到过温州的人,会对公路两边随处可见的教堂留下深刻印象。温州基督教与天主教信徒很多,在当地人口的占比也很高。目前,温州基督教徒有75万,天主教徒约有15万。如果加上没有登记在册的,两教信徒可能在100万以上,约占总人口的15%左右(数据来自学术期刊的整理)。
有意思的是,近代浙江,温州开埠时间(1877)远迟于宁波(1844)。开埠后,两教在浙江的传播主要在宁波和杭州一带。外国传教士驻在地在宁波出现是1843年,杭州是在1859年,温州则在1867年才出现。何以两大教能在温州大行其道,甚至温州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有一种解释,认为地理环境是重要原因。温州四周群山连绵,相对闭塞。从地理位置上看,正好处于吴越文化与闽台文化的临界点,文化身份相对模糊。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位置,使旧体制禁锢性政策约束力相对较弱,传统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温州影响不大,容易受外来宗教与思潮影响。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温州以南的闽粤一带,相对来说更加偏远,为何没能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笔者以为,这可能更多与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有关。
在诸多关于温州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温州人善于抱团合作。良好的内部协作,是温州人最突出的品格,远甚于温州人自己概括的“敢为天下先”精神。温州人内部协作,往往借助于亲戚、好友、同乡等渠道形成的“强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利用这种强关系,温州人开办家族企业、家庭手工业,或者抱团外出务工、经商。北京的“浙江村”和国外的“温州城”,大多就是这样形成的。温州人每到一地经商,都会建立温州商会,即使买房也形成“炒房团”。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既是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他们流动得以持续的机制。
温州的宗族势力盛于其他地方。与随处可见的教堂、佛堂相映成趣的,还有数量众多的祠堂。与此同时,温州人形成强连带关系另一种途径是结盟。在青少年时期,情投意合的好友结成“盟兄弟、盟姊妹”,将超越血缘关系的同龄人结成强连带关系,互相帮衬。温州人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个人之间的感情纽带,出于互助互利的愿望,因此是一种“目标培养”式的关系。即人们有意识地去培植与另外一些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很长的时间后才能起作用。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温州人会结成这样一种强连带的协作关系?
笔者认为,温州这种工具型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自然环境内生选择,并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首先,是“稻作文化”及应对滨海平原多自然灾害的环境,产生了抱团协作的需要。黄宗智认为,华北平原多旱作,农户间合作的需要既不经常,规模又小,南方多水稻耕作,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需较多人工和协作,这是南北宗族势力差异的生态基础。在温州,还需强调的一点是:由于人们主要聚居区集中于狭长的滨海平原(当地人称为“垟”),是台风、海溢、山洪等自然灾害多发区。面对自然灾害,温州人需要集体力量抱团合作;其次是人口多次流动迁徙的结果。温州历史上的移民,总体上具有“南徙而北顾”的特点。新移民的到来与原住民形成抢食关系,人地关系更为紧张。直到上个世纪末温州发生村庄之间、宗族之间大规模的“械斗”仍很常见,新来的移民必须结成更紧密的关系一致对外;第三是多元化职业内部协作的需要。除农业耕作,明清以来温州人的职业已多元化,如渔业、工商业、采矿业、卫所军人等,本身存在内部抱团合作的需要,因此形成了强烈的家族、乡党、教友、盟友的观念。
外来宗教正好契合了温州人抱团合作的内在需要。无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信徒之间极易形成紧密的关系。他们以兄弟姊妹互称,每周举行礼拜,中午常在一起聚餐。每一教区的教友往往建立基金会,由教友捐款,用于教会的公共支出及慈善事业。由于两教在温州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企业家中间也有很多信众,常一起交流心得和感悟,生意上也会互通有无。由于更强的信任关系,相互间民间融资也更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也可解释,温州的民间金融何以如此盛行。
可见,温州人通过宗族、结盟、宗教等渠道形成的强连带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出于 “表意型”的需要,它更多承担了“工具型”的社会功能。温州民营企业如此兴盛,绝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深刻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原因!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