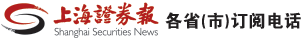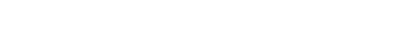何以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会一起上涨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像是对发达国家央行的一场考试,今天的“资产荒”似乎说明发达国家央行在这场考试中的成绩欠佳。这场考试后,至少有两个曾避免给予明确答案的问题需要直接面对:央行是否该对资产价格负责任、对微观金融稳定负有什么责任?
□许 鑫
当国人还在争论我国的“资产荒”究竟是相对于实体经济发展货币太多还是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收益率频谱缺失时,突然惊喜地发现,我们并不孤单,英国公投“脱欧”后,全世界都面临“资产荒”了。
说世界范围内“资产荒”,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避险资产和风险资产齐涨。英国公投“脱欧”后,世界资本市场面临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一起上涨。传统避险资产中的黄金、白银备受追捧,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的两周,国际金价累计上涨7%,银价上涨14%。另一种传统避险资产——发达国家国债——更为夸张。7月5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0.225%,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1.38%,双双创下历史新低,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0.16%,同样处于历史低位。此外,英国、意大利、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都创历史新低。一般认为,遭遇英国“脱欧”这种黑天鹅事件,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因此避险资产会上涨,但奇怪的是,股票等风险资产也在上涨。同期美股标普500指数上涨3%,欧洲、亚洲主要股指涨幅也都在3%以上。英国富时100指数更反弹9%,不但成功收复失地,还创下去年8月以来新高。对此,避险情绪显然不如“资产荒”更有解释力。
如果说我国的“资产荒”还存在货币过多和资产市场化程度不够的争论,那么世界的“资产荒”就只有一种解释了——钱太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的QE为代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进入了货币宽松时代。从2008年12月开始,美联储连推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于2012年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2013年,日本央行宣布开启新的无限期每月购买1450亿美元国债的计划。其中,仅美国,截至2014年已释放了3万亿美元货币。相对于释放出的货币,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却极为缓慢。除了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外,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迄今都仍未走出衰退的泥淖。欧洲的经济增长率徘徊在1%以下,意大利和德国再次面临银行业危机的可能,“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也没能促使日本经济走出零增长,而通货膨胀率也从2%回到了接近零的水平。
说实在的,当下的宽松货币政策,与其说是在拯救经济,不如说在避免危机。世人看到的事实是,货币发行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各国央行其实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就从未正常化过,经济政策要么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短期化手段,如美国货币政策QE是货币主义者本·伯南克所谓的“坐着飞机撒钱”,应对可能的金融系统性危机;要么是应对政治“黑天鹅”事件的手段,如英国“脱欧”公投,英格兰银行宣称准备了2500亿应对可能的经济波动;要么是屈服于政治的非经济行为,如为了推进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安倍晋三不惜撤换日本央行行长。
市场显然明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无异于依赖毒品在短时间内提振精神,因此寄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常态化。数年前,美国曾传出由当年铁腕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保罗·沃尔克重新执掌美联储的声音,就表现了民众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反感。当然,这个传言并未成真,但由于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国显然想尽快回归到正常的货币政策上。今年初,美联储提高利率就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步骤,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年内三次或四次加息的市场预期已经落空,看来今年最多也只有两次加息。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像是对发达国家央行的一场考试,今天的“资产荒”似乎说明发达国家央行在这场考试中的成绩欠佳。这场考试后,至少有两个各国央行曾避免给予明确答案的问题需要直接面对。
第一,央行是否该对资产价格负责任。这是个很有争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今天的社会里,资产价格远比商品价格更影响经济稳定,但格林斯潘、谢里特等曾经的数位央行行长都表示:在确定资产的公允价格方面,相对于市场,央行并无优势,且如果央行把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考虑因素,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虽然对这个问题没有结论,但显然,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确实把资产价格纳入了货币政策考虑中。现在看来,格林斯潘们的担心成了现实,资产价格完全依赖于货币政策。每次宽松预期来临,资产价格就上涨;每次加息传闻出来后,市场都会以股价下跌报以颜色。央行到底对资产价格负有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急需给予明确回答,否则,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还是会在股市的上上下下中起伏,犹如被资产价格裹挟了一样,失去自主性。
第二,央行对微观的金融稳定负有什么责任。传统理论很清晰,央行需对宏观金融稳定负责,对微观金融机构,只有在其破产足以带来系统性风险时,央行才能施以援手。但现实并非如此。在金融危机时,发达国家的央行曾数次救助金融机构,但为什么贝尔斯登和雷曼就不需救助,其他大的投行就需要救助呢?在危机后不久把金融机构划分成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用何种标准做这样的区分?既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得到央行特别“关照”,又该如何特别予以监管?现在,央行扩大权力似成国际潮流,当央行越来越多地陷入微观机构的监管中,如何避免微观金融机构救助普遍化及由此带来的货币发行问题呢?
除了央行,整个经济界可能也不得不思考一个更为宏观而且缺乏明确答案的问题:央行及货币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负有什么责任。每次经济下滑,市场和政府都希望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从长期来看,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作者系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