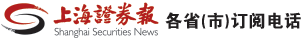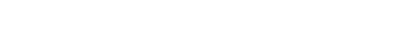专业新闻主义的防线与底线
|
——评《王国与权力》
⊙杰 夫
在美国访学的那半年,每天早晨我都会买份《纽约时报》,这成了习惯,或者说,是对新闻阅读的一种姿态。
按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中的描述:“《纽约时报》单独地、稳固地、不可动摇地屹立着。它是过去和现在永恒的混合,是一个中世纪的现代王国,有它自己的私法和价值……《纽约时报》是《圣经》,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携带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作现实来接受的生活观。人们按照一种简单的理论来接受它,即凡在《纽约时报》上出现的事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盲目的信仰使得《纽约时报》的许多人成了修道士。”
长久以来,《纽约时报》给公众的印象是专业、严肃且有时不免冗长,它代表和传递的是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在这份报纸版面上,没有血腥暴力,没有八卦绯闻,没有捕风捉影,它对影响国家和世界发展进程的人物与事件感兴趣,并予以中立的、极具专业精神的报道。所以,这份报纸一直被西方舆论视为负责任的“时代的记录纸”。从品质与调性角度看,能与其媲美的或许也只有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学人》杂志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你不急着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等一周后出版的《经济学人》来告诉你——对媒体而言,这可是极高的肯定。
“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这是《纽约时报》的宗旨。然而这句标语可被解读为两层意思:一是无所畏惧,揭露真相,实现正义;二是负责报道一切,还原客观真实。这其实也是两种对新闻与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的观念分野。有种观念认为,新闻是行使公众监督权的工具,报社应去质问和揭露政权,从而实现社会普遍的公义。也就是说,新闻是实现社会理想的工具。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不过是对纷繁的社会现实的记录,目标不过是向公众提供专业记者编辑所探索到的、了解到的真实。至于对社会正义的判断,权力并不在新闻手中,乃是社会的责任。换句话说,新闻不过就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而已。然而,对一家报社而言,这已不仅是学说之争。往小了说,它事关报纸的品牌定位、经营路线;往大了讲,它涉及议程设置、权力之争。
所以,盖伊·特立斯为《纽约时报》写传,书名就是“王国与权力”。而在长达630多页(中文版)的篇幅里,他一直在讲述《纽约时报》从19世纪中期被奥克斯家族购买之后,出版人、总编及一些重要的记者、编辑之间的斗争。
因此,若把这本美国新闻学经典著作理解成一部《纽约时报》企业史,未免太过简单。特立斯之所以对《纽约时报》发展初期一直延续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编辑部里的故事”兴趣盎然,那是因为他懂得当奥克斯-苏兹贝格家族试图去平衡报社的重要编辑之间的关系,以及报社潜在总编、各个版块的编辑之间彼此倾轧、钩心斗角以取得对最终和实际控制权的一系列事件中,其经过堪称惊心动魄、生死攸关。这是牵扯一个资讯和舆论王国的“王权争夺”。
看看艾伦·布林克利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詹姆斯·莫瑞斯的《普利策传:一代新闻大亨的传奇人生》、哈罗德·埃文斯的《底线: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自由》等便可知,编辑控制权的争斗可从来不是游戏。多少年来,类似戏码一再上演。除了话语权和利益上的考虑,权力之争关乎的是新闻自由、职业伦理与公共利益究竟倾向哪边——对新闻人而言,这既是要警惕的防线,又是须坚守的底线。
《纽约时报》在《世界报》随着普利策离世而轰然倒塌之下迅速崛起。面对《新闻报》(后改名《美国人报》)倡导的“黄色新闻”,它坚持严肃,绝不跟风,再加以得当的经营策略笑到了最后。经历了百余年发展,面对数字时代的冲击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虽然发行量有所下降,但在当今纸媒的领导地位岿然不动,并一直在致力于媒体融合的创新报道。所以,在特立斯的这本《王国与权力》中,我们看到了《纽约时报》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遵循专业新闻主义,崇尚真知真相,行使社会公器监督权力。用我们熟知的话来讲,那便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其对立面往往是以轰动性新闻、巨量发行和影响力吸引最广泛的读者,在赢得商业利益的同时要挟政权,获得某些法外特权。
值得一提的是,特立斯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并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尚先生》(Esquire)等杂志撰稿。他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种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手法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刻画细节不遗余力。特立斯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作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
请看这段:“新闻编辑部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正如一位访问记者注意到的,这里有时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馆运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桌旁的记者们会靠在他们的椅子上,品尝咖啡,读报纸,观察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经常在一个办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张桌子边聚会,也有时下班前这个地方是平静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谈情说爱的男人和女人,会在高级编辑去参加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后,溜到时报广场附近的某个饭店里约会,只是别忘了给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偶尔打一个询问电话,然后在6点20分之前返回办公室,因为这时城市版主任会沿着走道溜达,例行常规地跟上早班的每个人说‘再见’。有个叫艾伯特·J.戈登的记者,有次在一天结束时没等到主任说‘再见’就回了家。后来他接到了电话,主任说想跟他讨论一件最重要的事——现在,当面。戈登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不方便,此时还下起了雨,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编辑部。他到那里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点儿愠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会儿,这位主任却只是抬起头来微笑着说:‘晚安,戈登先生。’”
这种写法,场景极细,枝蔓极多,在讲述一件事时会插入其他有关的事情和人物。这也为阅读本书增加了难度。但正如特立斯及他曾经工作过的《纽约时报》,选择看这份报纸,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智识训练和所谓的阅读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