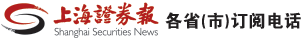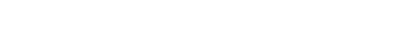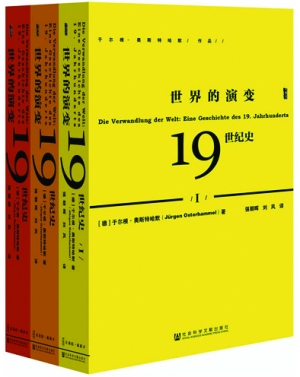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前一波巨浪
| ||
|
——读《世界的演变》
⊙林 颐
我们生活在21世纪,周围发生了很多大事。2016年,我们遭遇了人机大战、英国“脱欧”公投、德国难民问题、法国恐怖袭击、美国大选……当下变成历史,往昔缔造未来。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个利益大小的问题:它们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是一部关于19世纪的历史大作。它不是通史,而是有关“历史的历史学”。叙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更是为了在这些历史面貌之中抽离出历史观念。作者所关心的不是通常所见的对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要创建一种体系:在记忆与自我观察,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里,通过全景式扫描和更细致的主题研究,对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因素作显像分析,让世人领悟社会历史表层下盘桓极深的趋势性脉络。
“时间”与“空间”是造就历史的最基本元素。但机械的划分法必然会割裂历史的内在联系。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长世纪”理念,将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20余年全部纳入19世纪范畴。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之三《帝国的年代》就是如此。霍氏认为如此可较完整呈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于尔根采取的也是长世纪时间概念,但他用了大量篇幅阐发众多史学家的年代划分法,这就是于尔根的治史态度,从一开始就强调他的用意在于探索一种历史模式的构造。
通过对“元地理学”、地理大发现,以及美洲、远东等古代历史的回顾,于尔根确定19世纪的主角是欧洲。不过19世纪的空间形态并不是僵硬的,支撑它的重要结构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向外辐射,又向内吸引,边缘则较多表现为信息接收者,在不同的边缘位置,总有新事物不断涌现。中心和边缘有时是变动转移的,有些边缘在某些主题里会成为主要解构对象。
在阐明19世纪时空的界定时,于尔根解释了他所采用的文本分析的材料来源:视与听、记忆藏所、叙述、报道、统计学、新闻、摄影术……凡此种种,其核心都是“记忆与自我观察”。有关“历史记忆”的历史,体现出于尔根的历史哲学观,他所说的“记忆”包含了一种宽泛的文化传统,我们很多人对于历史都有个坏记性,而且往往没有意识到正在经历遗忘或修正。而本书对此悄悄发生了一场渐近的记忆修复,随着全景的展现和观察对象的逐一推进,过去的经验部分将重新浮现,并融进我们对当下世界的理解。
以19世纪的“全景”观之,尽管我们以后见之明得知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纪,它将通往1914年8月那个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但19世纪的人们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发挥作用的力量并非来自任何一方,而是有着更广泛的动因。这些力量环环相扣,共同形成了历史的合力。
全球化让民族迁徙成为常态。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对人口问题做出了反应。拿破仑战争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引发大饥荒;黎巴嫩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移居美国和埃及;对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而言,移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进程;加勒比地区的废奴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全球移民动机证实了普遍性经济规律,同时难免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亨廷顿说过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至今日,它依然伴随着疼痛和相互攻讦。
19世纪,世人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生活水平”与“生命质量”。有关工资、寿命、公共卫生体系、疾控标准的统计学数据展现出让人欣慰的进步。曾经让欧洲大面积陷入恐慌的“黑死病”和造成美洲灾难的大瘟疫,都有了免疫的科学武器,人类生命得以拥有隐形的保护伞,但马尔萨斯以他的洞悉预见到了人口大爆炸的危机。显然马尔萨斯对农业前景和科技成就过于悲观了,但对21世纪的我们而言,负载过重的地球是否还是宜居的家园?
尤其城市的居民。卡尔维诺说,当穷尽城市的所有形式之后,城市的末日就来临了。他告诫我们:“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19世纪的城市增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受到市场和资本因素的推动。巴黎、伦敦、纽约、曼彻斯特……几乎所有超级大城市都在这个阶段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城市呈现出水与火的双重属性。我们对城市的感情很复杂,它既是对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又是让人们实现梦想的飞翔之地;它既是罪恶滋生或难以驾驭的逼仄空间,又是西西弗斯式超脱平庸日常的精神象征。
19世纪的一个重大发明是“民族国家”。于尔根并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但这部分在书中的占比足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帝国与民族国家是19世纪人类聚居的两大政治单位”,这组关系的对立是构建当今欧洲版图乃至整个世界政治区域的最重要因素。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有过骇人暴行;它肯定不是现今国外仅有的破坏性因素——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个人对权力的追逐、非民族的利益等等,一直都是,现在还是和民族主义一样具有颠覆性,一样残忍和暴烈。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于尔根把英国作为帝国典型案例是明智的选择。对英国19世纪历史的回顾,赋予我们一种在不同切片里对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帝国日暮症候群加以诊脉的方法。
为了解释英国在20世纪的衰落,不仅要全方位观察大不列颠,还要考虑欧洲悠久的地缘政治传统,以及热带非洲、美洲、俄国、印度和远东的社会发展状况。民族主义逐渐成长为压倒性势力,它与强权、革命、宗教改革等势力此消彼长,并在相互消解和相互融合中吸收利用了这些势力的力量。对国家落后的痛切体悟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掀动的革命高潮席卷了欧亚美非各地区,缔造了20世纪的两大阵营。即使如今冷战已结束,其遗留的政治遗产仍然发挥着影响力。
为了解剖各个局部,必须首先把目光集中在整体,于尔根对全景的把握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视野。构成这个全景的主要局部,包括:能源与工业、劳动、网络、等级制度、知识、“文明化”与排异、宗教。它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主题”中得到更具体的阐述。
这些构成可以把握的整体的局部都是些什么呢?如何发现它们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边界?于尔根的分析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就经济而言,19世纪是“煤炭世纪”,工业化生产方式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广为传播,消费主义开始兴起;就政治而言,社会领域的垂直维度被打破,贵族阶层衰亡,市民和准市民成为主导,民主政治替代了君主制;就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宗教世俗化和科学逐渐占据上风的时代,知识成为国际化流动的产品,而意识形态则是文化输出的重点。于尔根在全书开篇就引用了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的比喻,19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这张“人类之网”密密织就的过程。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织,以及人类对此做出的各种反应。
在19世纪的世界演变历程中,在“人类之网”的形成之间,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于尔根一开始就声明他秉持“欧洲中心论”,但纵览全书,也不乏散点式论述,比如美洲、中东、南亚等地区,都在某个阶段成为笔墨所向。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历史和宽阔疆域的大国,必然会在书中不时闪现身影。在18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面对迅速膨胀的人口,中国农业仍然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但中国农业到了19世纪初就失去了好运气。伴随自然灾害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国的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剧烈动荡。恰在此时,欧洲列强打上门来,汹涌的全球化趋势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这是旧时代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开启。
今天,世界各国一起经历着人口压力、贫富分化、金融危机、生态困境、灾异气候……在越来越紧密的人类联系之中,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对历史研究而言,从来没有过去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