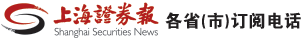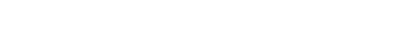由钱荒催生的宋朝纸币实验
|
宋朝的财政与货币制度对纸币在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纵向流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塑造了货币在宋朝经济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环境。作为世界最早的纸币实验大国,宋朝在尊重民间规则的基础上,顺应经济货币化趋势,因势利导地推进纸币实践。
回顾历史,钱荒并不是新鲜事。
从唐代开始,官方政策从严禁私铸转向严禁百姓挟钱出境、严禁百姓毁钱铸器,可见钱荒现象已经很频繁。到了宋代,铜钱的匮乏使得铜钱外流成为热门话题,热门程度类似于后来的白银外流。当时用“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来形容铜钱流向边界甚至海外。在新书《白银帝国》中,我叙述了宋朝立朝之后的制度继承前制,经济方面对于铜钱流向邻国与海外很是警觉,多次下发各类禁令;与之相对,在这场货币战争之中,金、西夏等国则是用各种方式吸引铜钱,例如走私、越界采铜、运用短陌等方式。当时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对于铜钱更是趋之若鹜,往往把价值10倍的商品只卖一成,只为带走铜钱。虽然明代也有少量中国钱流入日本,但是宋钱数量远多于明钱,影响甚为广泛久远。
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件大事:王安石启动变法。王氏政策之一是废除钱禁,收敛民间财富,充实政府。禁令一出,宋钱加速外流,钱荒更加严重,这方面的记录俯拾皆是,比如神宗年间就有这样的记录:“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钱荒之下,钱贵物贱,宋廷大举铸钱,加之以免疫法攫取民间铜钱,府库很快满盈,而民间则商贸凋敝,不乏交不起税而变为流民之人。
铜的缺乏使得铜钱的铸造相对前朝而言偷工减料。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铸281万贯铜钱,合计减料878000余斤,而这些料能够再铸造169000贯铜钱,这也使得宋代人更欣赏前朝货币,例如唐代的开元钱。到了南宋,当时人更是感叹“物贵而钱少”。我在《白银帝国》中就列举过,以会子诞生的绍兴30年来看,其目标是铸造50万贯铜钱,结果只铸造了10万贯。
宋朝是否真的缺钱?以铜钱为例,其实宋代铸造了不少,学者高聪明统计整个北宋时期的铜钱铸造量达26200万贯,这还不算旧钱。而彭信威估计当时全部货币流通量为24000万至25000万贯。日本宋史研究者宫泽知之认为,流通中的铜钱大部分都以各类税收方式回流国库,一年大约有7000万贯之巨。因此,流通中的铜钱没有这么多。但美国学者万志英认为,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朝廷几乎以与收入一样的速度将国库中的钱不断花费出去,因此流通中的铜钱数量仍旧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高聪明估计11世纪末的商品流通总量为15000万贯。如此来看,与商品流通总量相比,宋代铜钱并不算少。
也正因此,钱荒并不仅仅是铜钱的缺乏那么简单,正如学者朱嘉明所言,中国自汉朝以来钱荒不断,其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换言之,是经济的繁茂而不仅仅是贵金属的匮乏导致了钱荒。
这一矛盾在宋代十分突出。一方面,大量铜钱被窖藏或者外流,没能有效流通;另一方面,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如现代银行这样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的情况下,铜钱数量难以精确对应商品交易需求,可以说宋代的钱荒本身也是经济需求发展的表达。我在《白银帝国》中引用了日本学者斯波信义研究,宋代区别于前代的特征在于,地方性市场、地区性市场、长途贸易与国际贸易在宋代都得到了广泛发展。
贸易繁荣决定了铜作为货币已经独木难支,各地随即涌现了不同种类的货币,铁钱、铜钱、纸币、白银都曾作为货币流通,这事实上催生了中国成为最早的纸币大国。随着民间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无论交易数额的增加还是交易半径的增加,都需要更简便更高面额的货币,无论是最初的纸币还是随后的白银,其实都比铜钱更有优势。《白银帝国》多次讨论过货币的约定性质,从留下的史料看,只要取得民间信任,各种形式的货币都可能流通,其信誉高者甚至可能溢价交易。这在北宋的货币实践中有充分的反映。
在民间信任的基础之上,如果政府以正确的方式介入货币管理,所谓法币即可能诞生。以北宋交子为例,国家一旦发行纸币就带有法币性质,其信用建立在国家承认其价值的基础之上。金属本位的纸币意味着纸币直接与实物货币等价挂钩,维持了其信用:会子开始与铜钱直接兑换,并且可以用来和政府交易,可以作为购买盐引、茶引等有效价值凭证,并交纳赋税。所以日本学者宫泽知之认为,宋朝的财政与货币制度对纸币在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纵向流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塑造了货币在宋朝经济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环境。高聪明则认为,这一纵向流动之所以成立,也是基于范围广大的货币民间交易的横向流通。
作为世界最早的纸币实验大国,可以认为宋朝在尊重民间规则的基础上,顺应经济货币化趋势,因势利导地推进纸币实践。只是好景不长,随着纸币的发行到滥发,随后的失败则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了。
(作者系青年学者,近期出版新书《白银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