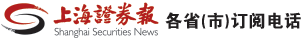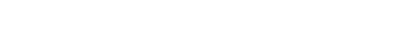人类能克制
日益膨胀无所不在的欲望吗——读《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
| ||
| ||
|
⊙禾 刀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吸引世人眼球的地方很多,比如特别的发型、特立独行的“大炮”风格,但最吸引人之处的当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人本性——他不放过任何场合、任何机会,想千方百计拉动美国经济也即GDP的增长。其实,不仅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领导人对GDP寝食难安,因为GDP数据不佳而丢掉总统宝座的政治人物比比皆是。GDP就像一根难以预知的魔法棒,有时给人欢喜,有时令人痛苦,有时还会诱发战争。
GDP因何而来?GDP又将往何处去?这是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呕心沥血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作为科学作家、《自然》和《新科学家》杂志曾经的编辑,伊桑·马苏德在《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中以提纲挈领方式,简要梳理了GDP被人为制造、被人为推崇膜拜至而光芒四射的“发迹”历程,而他笔下还有诸多知名人士对GDP的质疑与反思,这才是本书的落脚点——如今GDP 何以成了“众矢之的”。
应运而生
1933年,深陷在大萧条中的美国,还看不出任何提振经济的希望。那个时候,美国太需要有个能真正测定市场经济繁荣程度的晴雨表了。此时,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经济学学者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扛起了这个重担,开始着手搜集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一年后,他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国民收入,1929-1932》——GDP由此出世。
在那个电脑尚未曾听闻的年代,为了摸索一个测定公式,库兹涅茨只能和他的小组一起跑遍美国各地搜集数据,然后投入大量枯燥的运算和分析。虽然库兹涅茨得出从1929年至1932年美国国民收入几乎减半的结论与大众感受“神合”,虽然库兹涅茨这份报告当年取得了4500本的可观销售成绩,但这些均未促使GDP走红。
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如果不是美国急于了解欧洲的繁荣水平,库兹涅茨发明的GDP很可能在1932年后便悄无声息直至被人们淡忘。“二战”结束后,合计130亿美元(若考虑通胀因素,这笔援助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万多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启动在即。如同每位资助者的本能心态,美国当然不希望这些援助打水漂,所以想适时掌握欧洲的经济状况,想了解援助究竟会给欧洲带来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GDP被委以重任。自此,GDP声名鹊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时至今日,定期公布GDP值已成各国反映市场经济繁荣程度的“规定动作”,当然也是各国政府面向国民的一次次交卷。正因如此,“即便GDP出现最小幅度的下跌,也会被政治对手当作经济决策无能的证据”。各国间围绕GDP展开的拼搏赶超令人眼花缭乱。
回过头来看,GDP的历史贡献理当肯定,但同时更应看到,库兹涅茨的发明之所以被大力推广,实得益于“马歇尔计划”。正因为“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渴望尽快得到美国的援助,客观上存在推广GDP的动力。待到欧洲经济逐渐走出战争创伤的阴霾,及时公布GDP值已成欧美测定经济繁荣程度的共识。或者说,欧美战后经济所取得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也是顺应GDP统计的结果。
弊病丛生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GDP并不热衷,他认为“GDP既不能衡量幸福水平,又不是幸福指数,因为GDP体系在制定之初并不是为了表明消费与投资行为无法反映的重要生活现象”。《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更一针见血指出“GDP又不能当饭吃”。
在批评者眼里,GDP非但“不能当饭吃”,还弊病丛生,甚至有“毒”。当世人从对GDP的狂欢迅速发展到盲目崇拜后,GDP负面效应愈加“夺目”:“GDP数据稳健的国家很可能有大量国民深陷债务之中”;“稳健的GDP数据会隐藏根深蒂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很多新兴独立国家虽然贫穷,但是表面上却显得很富有,原因就在于高昂的军事支出”……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石破天惊,向读者呈现了那些不管社会环境、几乎不受控制的化学品生产乱象,科学家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人类合成但难于降解的农药DDT。该书“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引发了美国社会长久且激烈的争议。
GDP对环境的肆意伤害只是一方面,透支资源更触目惊心。1972年国际科学家团队撰写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无异于扔向GDP的另一枚核弹。该报告指出,“预测显示,如果世界经济持续目前的正常发展路径,人口继续增长,各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挖煤、钻油、生产食物并排放大气污染物,那么到了2100年,社会与环境就会崩溃”。25年后,科斯坦萨及其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得出了“增长的极限”的定值:33万亿美元——“如果全球GDP(当时)中涵盖环境和‘自然资产’预算,那么很可能会增长到33万亿美元”。马苏德虽然认可当下科技力推的洁净技术,但同时认为这“只能推迟地球上生命维持体系的崩溃时间,但是却不能避免这一灾难”。事实上,关于人类大发展生物大灭绝的“危言”近年间不绝于耳。
盲目追求GDP,不仅资源难堪重负,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看来,GDP并不能等同富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学有所成的哈克回到自己的祖国巴基斯坦,通过所学经济知识为祖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哈克逐渐发现,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却是贫富差距的拉大。1968年,哈克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一个“22个家庭”的故事:一方面巴基斯坦年经济增长率高达6%,并创造50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全国22个家庭拥有66%的工业公司、79%的保险资金以及80%的上市银行。而在近半个世纪后的美国,类似现象依然令人瞠目结舌: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
关于GDP弊端的论述还有很多,不少有志之士提出了大量改进建议,但GDP与社会经济还有领导人政绩已高度捆绑,形同合体。在数十年的习惯面前,任何改弦更张的念头均意味极大的冒险,因为这并不是换掉几个数字那么简单,很可能涉及经济秩序的重建,还有政绩评价体系的重构。一次GDP数据的异动,便会搅得市场风生水起,政界常常为此焦头烂额。所以,GDP的地位一时半刻还难以看到被撼动的迹象。与其说这是历史惯性使然,不如说与GDP关联的利益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去向成谜
150多年前,面对凶神恶煞的美国白人,印第安人部落领袖、西雅图酋长在《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会降临到人类身上……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酋长生活的时代没有GDP,但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了万物,也就不会有人类。放到今天看,酋长的这番理论仍然光彩照人:即便GDP塞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人类就不可能拥有一个适宜的空间——当地球只剩下人类的时候,人类不可能幸福,只会在孤独中灭亡。当然,回到丛林时代也并非人类的理想选择,人类的福祉绝不是在饥寒交迫中时时还得提防猛兽和自然灾害的侵袭。
马苏德在书中也描述和剖析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的幸福指数,还重点推介了联合国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综合来看,无论是不丹的幸福指数,还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两者均特别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这一理念在北欧诸国得到了较好倡导,而对更多国家特别是那些贫穷国家而言,确保国民不挨饿则是头等大事。
我们相信,假以时日,新的更科学的经济繁荣测定方式迟早会出现。现在的困惑在于,那些可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更有利的全新测定方式,未必就能碰上GDP问世后那样被美欧一致推广的历史机遇。还有,那些拜GDP承诺而上位的领导人,又如何摒弃GDP统计而致力于更科学的测定方式呢?
曾几何时,贫困被人类视为最大的挑战。而马苏德的文字给我们更深的感受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贫困,而是人类自身日益膨胀无所不在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