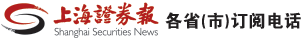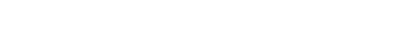士族衰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 ||
|
——读《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林 颐
就论述中国史骨架即时代划分这一问题,日本知名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过有名的“三分法”: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内藤先生的史学研究关注中国内部的阶层变迁,重点分析在政治、社会上中古贵族势力何以衰落,庶民力量何以上升,以及贵族文化的没落与以新兴的庶民阶层为主导的新文化的蓬勃。
内藤的“三分法”自然多有争议,而拥趸者也不少。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者谭凯 (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就是在内藤“三分法”的框架基础之上,聚焦中世向近世转变的关键时点,探析中古门阀士族消亡原因的著述。
从汉到宋,门阀大族上千年门第不衰。比较著名的世家大族,如北方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江南的陆氏、张氏、顾氏、周氏,南渡的王谢何庾等。这些家族,一般都有著名人物,如陆氏的陆逊、陆抗、陆机、陆云、陆贽、陆游、陆秀夫等。
门阀大族的衰落是从社会的流动加快,主要士族群体的流动加快开始的。士族流动加快的原因,一是来自社会动荡对士族的打击;二是来自士族内部不同区域集团和新旧势力的矛盾及争斗。东晋孙恩卢循之乱、萧梁侯景之乱和北魏河阴之乱等,无不严重打击了当时的江南士族和代北虏姓这些政治上显赫的宗族。在隋末农民战争期间,以社会底层的庶民及佃户、部曲、奴仆半贱民为主的农民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统一政权建立之后,经历多轮洗牌的士族结构变动必然带来多重矛盾和冲突。比如,关陇士族虽然处于上层核心地位,但因文化相对落后,其威望就远不如以崔、卢、李、郑等为代表的旧族。
谭凯的研究有个巧妙的切入点,即围绕唐代的墓志铭展开。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曾论述过墓志传记的起源,认为这与三、四世纪魏晋时期的一个法令有关。当时的朝廷禁止在墓地中竖立石碑,于是人们只好将石碑转移到地下,将其和死者一起埋在墓中。这些墓志因此保存得相当完好。墓志铭通常开篇追溯死者家族的历史,随后叙述墓主人的生平,主要聚焦他的仕宦生涯和公共形象,以华丽的骈体文称颂其品德和成就,最后以押韵的诔文概述死者功德,表达生者哀思。通过对墓志铭的历史研究,谭凯不但可以获取以上多重信息,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利用数学工具和分布图,分析各地的人口结构,包括成婚年龄和死亡年龄、子女数量和迁移信息,并由此推展至精英阶层的地理分布,家族和婚姻网络等情况。
通过典型样本,比如柳宗元的远亲柳内则的墓志的分析,谭凯剖析了唐朝的门阀观念。例如河东柳氏,表示来自河东的柳氏家族,并不意味着他卜居于兹,而是表达一种久远的家族身份的认同。郡望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非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郡望意味着“精英家族祖籍所在的郡”,意味着大族崇高地位的持续不衰。这些大族通过联姻,构建了牢固的人际网络,“外人”很难打进他们那个封闭的圈子。《新唐书》记载,唐文宗欲嫁真源、临真两公主于士族,不意应征者寥寥。文宗大为感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由此可见,在影响士族地位变化的要素中,崇尚郡望、婚姻的意识观念变化最慢。
在解释历史上那些声威显赫的大族失势的原因时,学者普遍认为是科举制度兴起所致。谭凯反驳了这种观点。据他的分析,唐代仕途荫举与科举双途并进,门阀大族严密地把持了前者,即便是后者,因为士族向来有文化教育的传统,庶族通常也是很难跻身其中的。根据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中的研究,唐朝时仅有10%的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谭凯的数据收集,官职的链条式图样,更加直观地确认了仕宦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武则天为了与反对她的高门大族的力量抗衡,设置了大量新官职,并且运用进士科考试作为获得高官的特许途径。曾经一度改变了士庶的力量对比,但这并没能动摇门阀的力量。很快,门阀士族就随着李氏王族的统治而回归。谭凯认为,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没能撼动士族,因为后来军权藩镇仍控制在大族手中。只是在唐末的黄巢起义摧枯拉朽、风卷残云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之后,才使得整个精英网络肉体上被消灭,由此彻底刨掉了大族的根系,原有的文化世界相应崩溃。
我国古代的门阀大族自后汉时兴起,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末,几百年盘根错节,从兴起、发展到消亡,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谭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屡次提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姜士彬(David G. Johnson)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笔者参阅该书,发现姜士彬对门阀大族的发展也有数据统计。姜士彬推论,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5%,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时则接近74%,而北魏、西魏和北周都超过了75%,东魏北齐的比例则在60%左右,唐朝初期降至56.4%,后期则为62.3%。而在北宋的第一个世纪里,宰相来自这个大族群体的比例只有大概2.5%,宋代的40名宰相,有22名明确和唐代大族毫无关系。显然,唐、宋之间统治阶层在这方面的确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谭凯的研究和姜士彬异曲同工,在史学的承袭上则为内藤湖南的“三分法”提供了依据。不过,笔者认为谭凯的论证仍存在一些解释不周之处。
谭凯在第二章“权力的地理”中,通过分析“洛阳或长安精英在地方的住宅分布图”和葬地分布图等,肯定了国家精英、高官权臣云聚京城的情况,也谈到了因此带来的房产价格上升而导致的周边卫星城的兴起,以及由京城向任命地持续而缓慢的迁徙。但他对另外几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的论述不足。比如,唐代的科举仅在京城举行,士族子弟欲为官者,只能集中在京城以求发展。《通典》曰:“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这正说明了科举制度的巨大吸引力,它首先是在士族内部的上、下阶层中引发了流动,继而扩展,终使人们意识到打破阶层固化,以及超越门第声望的贤能政治的好处。人口聚居的后果,迫使那些财力不足的京城世家不得不迁出京城,促进了地域间的家族流动。当时还出现了高等士族嫁女卖婚的现象。《唐会要卷》记载唐太宗言:“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所以,士族的家庭、婚姻网络并不像谭凯所说的那么严密。墓志铭的一大问题,就是谀辞满篇而绝不提半点丑话、坏话,这是研究者必须万分小心的,因此,某些论断还需要别的材料佐证。
另外,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暴露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安史之乱”则进一步造成流民的泛滥,谭凯看到了军权的更迭,但对流民现象却一笔带过。世家大族迁徙奔逃,重建秩序,军事力量兴起,加剧了唐末的社会动荡,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居他乡,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必然大大削弱。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以代替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实质上就是以贫富差别取代门第差别,这促使了大家族的瓦解和宗族成员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唐末农民起义其实就是这些社会危机积累、爆发的后果。黄巢的最后一击,“凌辱衣冠,屠残士庶”,烧毁了作为凭证的官私谱牒,终致士庶界限泯灭。
欧阳修撰《新唐书》,对士族衰落的过程有过总结。欧阳修从“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汨丧廉耻”谈到门阀制度的弊病,接着说到唐朝时的情形,“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然后举例大族的社会地位之崇高,“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感叹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这段论述可谓十分恰当。谭凯分析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时,注意了墓葬资料的静态显示,但动态趋势观察似乎不够。无疑,他提供的方法论是有价值的。正文之后附录了“配套数据库的使用方法”、“估算晚唐京城精英的总量”、“九世纪出土墓志的来源”等数据资料,这是他对中古历史的重要贡献,或能开拓学界更有深度、广度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