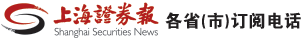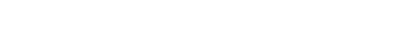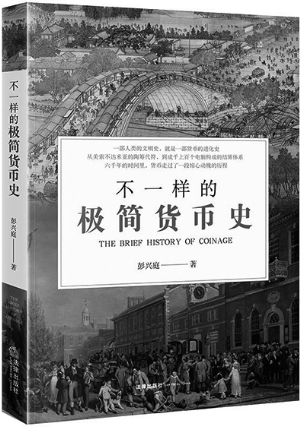换个姿势转个角度,就能看到另一种景观
|
⊙彭兴庭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货币变迁史。
公元前4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货币隐藏在一套由陶筹代符组成的复杂计数法中。
公元前2000年,在古巴比伦,在城邦统治者的管理下,人们的交换主要是以类似临时凭证的虚拟货币(谢克尔银)为价值尺度。这些交易以楔形文字记录在泥板上,就像今天我们的交易记录以电子账本的形式躺在银行系统中。
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法老们用黄金铸造太阳神阿蒙的雕像、法老的面具,还将黄金做成各种饰物、器皿、祭品……在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下,黄金崇拜撒播到了两河流域、希腊等地区。从此,黄金就像脱缰的野马,开始在人类历史上驰骋。
1023年,北宋建立“益州交子务”,开始接管交子纸币。纸币的出现,表明专制王朝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绝对控制。
在同时期的欧洲威尼斯,他们发明的是“债务”。当短期债务无法满足战争的融资需求后,他们就创新性地发明了一种长期债务,并为这种长期债务建立了二级市场,利息成为交易对象。这是威尼斯乃至整个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转折点。欧洲人首先学会了如何利用时间纬度,学会了如何理解价值的跨时期转移。
随着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诞生,存款货币逐渐走上历史舞台。
时间进入21世纪,从信用卡、芯片技术、ATM机、二维码支付到数字货币,金钱已经完全变形。
货币扩展了人类的合作范围。通过货币的作用,几百、几万甚至几亿、几十亿的人口紧紧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协作网络。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犹如血液,在社会的各种新陈代谢中起着运输和补给作用。
在探索货币变迁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是怎样的?
在一个原始的采集部落,人们根本用不着货币。在一个扁平化的小农社会,通过祭祀、礼物交换、战利品分配等机制,维持社会的交易秩序。在一个垂直化的现代大生产社会,如果没有货币,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血腥和暴力、专制和独裁。在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有无数的可能。货币虽然给人类带来许多的困扰和争斗,从来都不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但却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西美尔说:“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意识、牵动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
看待货币的姿势有许多种,从不同的角度,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
第一种姿势:从货币形态学的角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十分沉醉于钱币本身的形制、文字和图形,并将钱币学寓于金石学内。唐代张子平说,“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这些钱币学家对王莽统治时期五花八门的货币兴致勃发,而对唐宋千篇一律的钱币则懊丧不已。但事实上,货币的整齐划一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在王莽千姿百态的货币形制背后,是老百姓的困顿不安。
那些金石学家们流连于片钞只钱之中,埋头于方圆撇捺之间,真正的货币史家则很少。自魏晋以来,《刘氏钱志》《顾氏钱谱》《古泉丛话》等钱币学著作不可胜数,钱币收藏家们更是群星璀璨。但在这些士大夫眼里,货币的经济性荡然无存。他们只是金石家、把玩家和鉴定家。
第二种姿势:是从货币史的角度。
在二十五史中,绝大部分都有“食货志”的章节,但除《史记》外,几乎都是流水账式的。欧阳修是古代金石学的鼻祖,可他编撰的《新五代史》,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竟然没有《食货志》。中国货币史研究的奠基人彭信威说:“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历史。”正是从彭信威和他的《中国货币史》开始,国人开始将货币形态的变迁、物价的变化、人民的生活、社会的意识、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于是,大浪淘沙,洗尽铅华,货币突然从万物众生中脱颖而出,穿着金甲圣衣,成为历史变迁的决定力量。从货币史的角度,货币不仅见证了雅典文明的兴亡,诠释了古罗马帝制和大秦帝制的演变规律,也决定了英法战争的百年荣辱;无论是“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的海晏河清,还是“五代十国”的浑浊乱世,都有金钱的力量在背后驱动。
第三种姿势:从货币理论的角度。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就建立了“轻重”的货币理论,提出货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并提出由政府垄断货币材料——铜的主张。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极力维护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为封建王朝健全货币制度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北宋时期,纸币诞生后,产生了相应的“称提理论”,设置纸币发行准备金保证兑现,以维持币值稳定,还建立了“钱会中半制度”,即在国家财政中铜钱和会子使用数量各占一半,以示两者地位平等。
在西方,18世纪初的时候,约翰·劳就认为,货币的数量影响着全体国民的财富,增加货币量可以扩大生产,因为贷款更加便利,投资更具吸引力。亚当·斯密判断,随着纯粹的信用货币(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社会相应需要承担的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加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了货币主义学派,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
人们总想通过一套完美的货币理论,驯服货币这头时常失控的野马。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历史上,货币理论家们很多时候只是放放马后炮。
赫拉利说,观察历史的走向,重点在于用哪种高度。当你站在10米高台,你看到的是从你眼底走过的人群和墙脚丑陋的垃圾。你无法分清这个世界的脉络。当你站在100米的房顶,你可以看到车来车往的走向。但你的视野依然只是城市的某个侧面。当你从10000米的飞机上鸟瞰大地的时候,你看到了壮阔的江河湖海,看到了连绵起伏的群山峻岭,它们在你的眼底错落有致。但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轮廓,无法看到里面的细节。如果我们站在太空的高度,用卫星的精密来看,那么,我们眼里的世界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不仅可以看到地球的经纬,也可以拉近研究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对货币史的研究,本书将尝试换一种姿势,采用一种卫星的高度。
第一,全球化的视角。
一部货币史,是一部全球史。货币是全球人类融合统一的一种重要工具,无论是贝币、黄金、白银,还是后来的存款货币、电子货币等,如果只是站在某一国的角度观察,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古代与东南亚之间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一条贝币之路。黄金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失踪,是黄金在各国流转的结果。17世纪白银进口大大减少,则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多学科的视野。
保持一种姿势久了,难免会感到厌倦、疲惫。那么,在讲述货币的时候,能不能多换几种姿势呢?无论是货币形态学,还是货币史、货币理论,本质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当我们比较西方铜币与中国铜钱发展的不同路径时,就有必要列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货币形态特征,在谈论纸币的创新时,离不开约翰·劳的《货币和贸易》,在提到存款货币的时候,不聊聊货币的乘数效应是不可设想的。
第三,更多的历史细节。
货币史也是人的历史。再广阔的时代背景,也是由一个个人物去创造、去实践、去感悟的。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要调高卫星的分辨率,拉近距离,观察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琐碎生活。就像郯城的那个王姓妇女,从铜币的余温中,我们感受到小人物的无力、无助和无奈。就像替纳粹制造伪钞的萨利,当他放弃所有的生命激情与幻想,靠着仅有的那点人生经验和智慧,去对付各种无以躲避的问题,我们感受到的是战争中一颗小棋子的卑微。
货币不仅是一个交换媒介,还是许许多多生命的无声见证。
黑格尔说,历史像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还有余温。那一枚枚用金属铸成的硬币,那一张张沾着汗水的钱钞,似乎还带着一丝体温,诉说着万古长夜中曾经的人和事、家和国,或泣或歌,或悲或喜。
(本文系作者为《不一样的极简货币史》序所写的序,本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