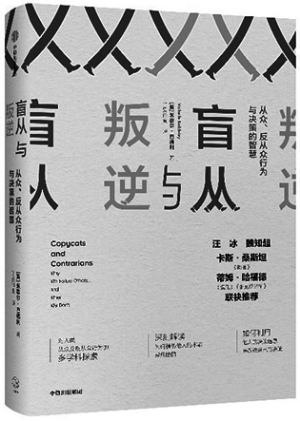效仿及叛逆本能
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读米歇尔·巴德利《盲从与叛逆》
| ||
|
效仿及叛逆本能
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
⊙潘启雯
效仿和叛逆本无好坏之分。盲从者与叛逆者其实都受到类似张力的驱动:到底是试图利用某个群体,还是在该群体中找到认同感并对群体作出贡献呢?在《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中,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名誉教授米歇尔·巴德利坦言:是成为盲从者还是叛逆者,由我们在不同背景和社会角色中的不同身份来决定。就好像电影《化身博士》里的亨利·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一样,一个在白天循规蹈矩、勤奋和专业的人,在夜晚则可能变得叛逆和充满破坏欲。
作为行为经济学界的重要学者,巴德利教授经常与社会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合作,她将经济学见解引入多种学科。她写《盲从与叛逆》的初衷,就是想借助社会学和生物学所能提供的真知灼见,填补经济学模型的疏漏,并更好地解释盲从者与叛逆者如何相互作用,效仿及叛逆的本能会否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当今的世界。
效仿可带来某种策略优势
许多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羊群效应研究者都专注于捕捉人的从众倾向性中隐含的社会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大致分为两类: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
信息性影响包括我们通过收集他人的信息而学习的所有方式。他人的行为及是否成功是我们可利用的重要信息。观察他人如何选择和决定,能帮助我们选择和决策。我们看到他人选择的结果,并从他人的错误和成功中汲取经验教训。从“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两个维度出发,巴德利教授发现,当我们迷路时,跟着大部队找方向就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效仿他人来收集信息和寻找方向,并以此为基础让自己做得更好。她把这种行为称作利己型从众。换句话说,选择从众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体能从中得到好处。从众可成为释放某种信号的方式,因而效仿他人可为我们带来某种策略上的优势;利己型从众可以是建立自己声望的途径;弱小的个体通过群聚可成为强大的整体;而群聚往往意味着安全。
其实,博弈论学家早已详尽论证了加入群体或团体带给我们的策略优势。其基本理念是一个自私的个体可与其他自私的个体抱团,并以团队形式在诸如狩猎等行为中完成单一个体无法企及的任务。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以狩猎牡鹿为例,阐述结盟如何为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带来益处。4名猎手在决定是单独行动还是合作组成一支狩猎团队。鹿体型庞大、奔跑迅速,更优的选择是4位猎手通力合作捕获一只牡鹿。假设4人能谈妥狩猎所得平均分配,那么这个同盟关系就能持续。对这个同盟中的每个个体而言,合作带来的好处大于单打独斗时的收益,因此联合狩猎是符合个体自身利益的选择,每个人都是赢家。
但是,以利己为导向的个体组成的团队并非总能带来好的结果。因为自私的个体会影响团队整体的行为和表现。当产出和回报在团队内共享时,个别团队成员或许会滋生偷懒或“搭顺风车”不劳而获的念头。除非团队中所有人的利益都能以某种方式保持一致,否则利己的个体就会毁掉团队的努力和付出。与这一关于策略优势的真知灼见一致的是经济学家关于理性从众的模型,理性从众选择是对效仿他人选择所能带来的额外收益的回应。当今最为常见的例子是一群金融市场交易员集体买入一个看涨股票,推高某一资产的价格并从中获得额外收益。
标新立异者总是剑走偏锋
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许许多多叛逆者,其中一些人成功地改变了生命和历史。从哥白尼和伽利略到达尔文、弗朗西斯·克里克(英国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詹姆斯·杜威·沃森(“DNA之父”)……如果没有如此多的标新立异者勇于承担特立独行带来的风险,现代社会将无从谈起。这些深谋远虑的标新立异者将我们带上新的征程——那些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无法想象、充满非议的征程。他们承担着丧失个人声誉及社会地位的风险,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深远变革。
巴德利教授的研究表明,盲从者之所以成为盲从者,部分归因于加入群体所带来的经济激励,而追求这种激励符合个人利益。叛逆者同样是由个人利益所驱动的,他们利用社会信息,建立自己的声誉,并在风险和回报之间寻求平衡,这与利己型从众如出一辙。同样,标新立异者也有强化他们个人优势的动力,但其表现形式则是与群体背道而驰。他们同样也在权衡经济激励,只不过是决定(与群体)相反的行事轨迹。他们的偏好使他们更有可能选择叛逆和反对。
1998年,发明从众模型的戴维·赫什莱佛及其博士生罗伯特·挪亚为了能界定标新立异者和叛逆者的行为,将“错配”概念引入了从众模型。他们主张,利己型从众会因为“错配”而受到干扰,而如果从众的群体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那么这种干扰就是一件好事。在赫什莱佛和挪亚看来,不倾向于随波直流、人云亦云的人也分好几种:“新来的”人或许因为加入时间过短,无法有效收集或使用社会信息,或出于某些原因被集体排除在外,未能有机会观察群体的行为;“先知”掌握着更优的私有信息,不太会受他人行动的影响;“过分自信的傻瓜”则是那些并未掌握更优质信息却自以为是的人,狂妄并错误地将自己的判断置于群体行为反映的社会信息之上;“反叛者”对收益的理解与他人不同,更有可能淡化他人选择中隐含的社会信息。
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德利教授还发现,大多数标新立异者都有个明显特质:盲从者避之不及的风险,他们承担起来却乐此不彼。这在金融行业的逆势交易者身上体现得最突出。从电影《华尔街》中狂妄自大、为获利而不顾他人死活的戈登·盖柯,到2015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传记电影《大空头》中,在逐利的同时多少还有点儿良知的逆市交易员,好莱坞亦真亦假地塑造了很多知名形象。部分行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做空了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初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繁荣时创造出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在泡沫破裂前,他们受尽奚落,而最终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对客观证据的合理分析揭示了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脆弱不堪,凭借这一先见之明,他们大赚一笔。但逆市交易的人在持异议时承担的风险极大。当其他人都在看跌某一金融资产时,选择看涨买入,不仅可能输掉一大笔钱,还有可能名声扫地。
那为何这些人还要选择承担逆势的风险呢?答案是因为对能赌赢市场的人而言,潜在的回报收益巨大。盲从者与标新立异者面对的风险都与一个经济学模型相关,即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伯恩海姆的一致性模型:一致性对关注身份地位的利己个体而言是有价值的,而对其他人而言,叛逆的价值更大。伯恩海姆认为,标新立异者有别于盲从者之处,在于享受其作为叛逆者的角色,以及剑走偏锋的倾向性。
“疯狂”发明家也是最典型的标新立异者。他们采用横向思维,并不太执拗于已有的做法,天资和能力都使他们能推进真正有用的发明。他们会给自己设定智力、机械工艺、商业等范畴的挑战,然后靠着内在的动力激励着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并非总是和群体背道而驰,只是更多独立于群体之外行事。
当共识的轨迹骤然转向时
经济学家的从众模型还显示,一旦我们认定他人掌握的信息更优,就会理性地跟随他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专家。麻烦在于,在宏观层面这会导致路径依赖。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韦斯伯格及其同事曾论证了这样一个理念:共识一旦过量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运用计算机建模的方法模拟了两类人群:一类由效仿型的“追随者”为主,另一群以叛逆者为主。他们创建了虚拟的地图以具化这两类人群分别能探索的知识疆域有多大。模型显示,以叛逆者为主导的人群所开拓的知识领域远大于以效仿型“追随者”为主导的群体。这个模拟实验带来的启示是,一旦专家群体中满是跟风者,对知识疆域的探索就必然是不充分的。效仿型“追随者”的专家因为互相效仿,所知会更少,因为从认知的维度看,他们本质上只是重走别人的老路罢了。相反,一旦专家群体中有了一定比例的叛逆者,结果就会逆转,知识疆域被充分探索发掘的可能性将大增。
诚如《科学革命的结构》作者托马斯·库恩所断言,知识演进的轨迹一般而言是平滑的,但当学习和知识部分是依靠社会互动完成时,这一演进历程就势必曲折多难。所幸,如库恩所言,当共识的轨迹骤然转向时,伴随“范式转移”会出现周期性的革命,从而实现知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