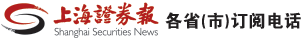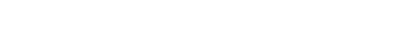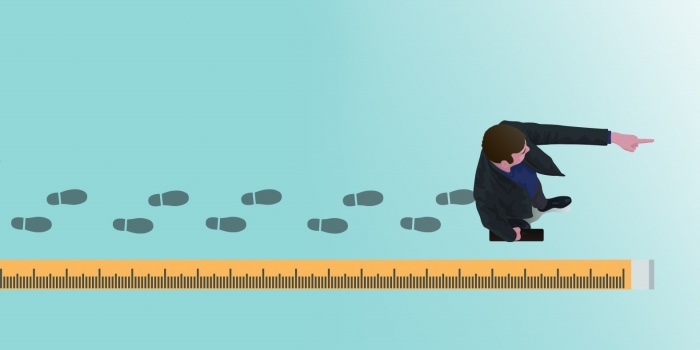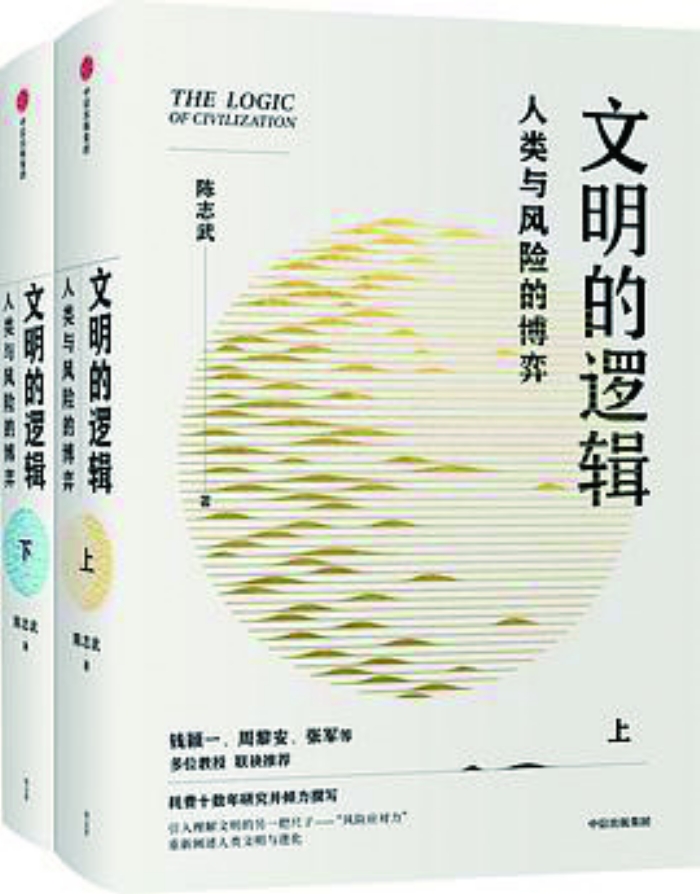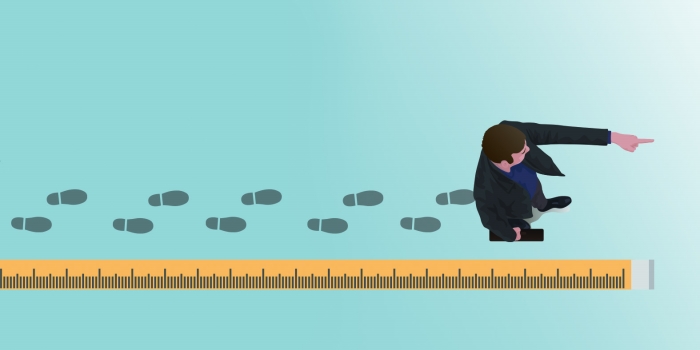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尺 ——读《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 ||
| ||
|
◎徐 瑾
当我们谈论人类文明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对此,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标尺。在主流经济学维度上,生产率是一把衡量文明的天然尺子。通过生产率这把标尺,人们就可以知道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会提高多少产出。对此,金融学者陈志武提出了补充意见。在他的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陈志武指出,生产率不足以概括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因而,在生产率之外,他又增加了一把新的度量尺子——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即风险应对力。
生产率不足以衡量文明
作者提出这个框架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看仅用生产率度量文明会产生哪些问题?如前所述,生产率可以衡量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测算标准也清晰明确,本身并没有不妥之处。但是问题在于,在农业社会,生产率即使在各地有所差别,也不会有本质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如果仅用生产率来衡量,就是一个长期的停滞阶段。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研究了全球GDP的历史演变过程后发现,在发生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换言之,在这段漫长时期,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化并不大。这个情况在古代中国也存在,比如汉朝时期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略高于清朝的道光年间。
因此,如果仅仅以生产率衡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说,生产率提升了一点,人口也会随之增加一点,总之人口的增加,往往会抵消生产率的进步,导致人均收入长期没有出现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经济学所谓的低水平均衡,即如今网络上流行的“内卷”。
在这样的衡量框架下,工业革命的发生就具备了划时代的意义。著名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教授就曾就说过:“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公元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这段话很典型地体现了经济学家单纯的洞察力,即他们虽然指出了人均收入提升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但是却忽视了人均收入提升之外的其他因素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价值。
很显然,如果只看人均收入,那么人类此前数千年的文明探索,几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带来多大意义。那么这段时间,人类是不是真的没有取得进步,或者就是在浪费时间?当然不是。作者指出,在过去 1万多年时间里,人类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的习惯,这背后的历程并不是生产率变迁可以准确度量的。人类社会的很多变迁,比如婚姻、家庭、文化和国家,也许对改善生产率没有带来直接作用,但是并非无用,同样创造了很多新的价值。我们不可否认,诸如家庭、国家等诸多因素,本身就是文明的内涵。
因此,抛弃“唯生产率”论的标杆,本身就是对经济学狭隘定义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人类社会和文明深度的探索。作者认为,“唯生产率”论的传统度量方法存在短板,甚至在宏观层面也有负面作用,会产生只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政策,是“唯GDP”论的基础。作者指出,人类文明的挑战在于,人类除了不断努力提高生产率,其实也在努力对抗风险。而相比生产率,对抗风险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另一把标尺
为什么抵御风险如此重要?作者认为,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由此可见,人类文明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风险不断降低的过程,也是暴力被驯化的过程。
人类历史大体符合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化,这背后的变化,可以从极端暴力的逐步减少来刻画。人类起源于原始社会,但是原始社会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安静平和。《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报道,原始社会的男性面临更多战争需求,25%至30%男人没有机会正常死亡,他们会死于战争或其他暴力。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等人研究,最近几百年间,战争次数在不断降低, “16世纪、17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1.5场战争;到了18世纪,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0.7场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中,只有不到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0.4场战争。”
除了战争,命案的死亡率也是极端暴力的体现。作者在书中引用相关数据显示,在原始社会,每年每10万人中平均有600人死于凶杀;而到了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则下降了不少,西欧在公元1300年的时候,大概是每10万人中平均有31人死于凶杀,20世纪则是每10万人中平均有0.8人死于凶杀。
也许在古代,普通人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所以才会面临诸多凶险,但事实上,身为人上人的统治者也不容易。根据作者等人的研究,古代的皇帝也活得很不容易。中国自汉代以来,共有 127个政权、 729个皇帝。其中,不少皇帝都是死于非命,最高点是7%;从唐代开始,皇帝们死于非命的概率才开始降低,到了清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降低到了 0.5%左右。
由此而见,无论是战争还是命案率,无论普通人还是帝王,其人身安全其实在数千年中不断进步,这些进步显然是文明的体现,但是这些进步在传统的经济框架中,无法用生产率指标量化,也无法检测。
那么怎样才能更全面地度量人类文明呢?作者认为,用生产率衡量人类社会文明显然独木难支,在此之外还要增加另一条腿,即风险应对力,人类历史就是依靠这两只腿不断前行。
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国家和信仰也许没有直接大幅提高生产率,但是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思路其实和投资一样,我们看投资,不仅要看回报,还要衡量风险。类似的结论,金融学研究早就证明过了,比如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里 ·马科维茨的论文就强调,最好的投资组合就是“一个投资组合是所有同样风险水平(均方差)的组合里预期回报最高的。”
规矩与秩序
作者在书中指出,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包括技术),而生活风险主要是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在这样的双重维度审视之下,对于知识或者说“何为有用知识”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即“只要是对提高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与之对应,作者将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 ,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前者和生产率有关,后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风险技能。
无论生产率还是对抗风险,其实与带有相对主义色彩的“文化”一词不同,文明往往意味着进步,与野蛮对应。这个词的流行,很大程度上,也与19世纪西方领先东方的大背景有关。 著名学者摩根索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归纳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段模型:蒙昧——野蛮——文明,差不多同时期东方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文明论概略》中,区分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文明”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作为名词的“文明”,指的是特定群体过去所做的一系列创新的集合体,这些创新给那个群体带来了生存秩序;另一个则是形容词的“文明”,是暴力与野蛮的反义词。他强调,文明的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贯穿其间的是“规矩与秩序”。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大家一直在指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但就整体而言,人类的暴力指数其实在不断降低。
毫无疑问,作者开创了新的研究框架,为度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提供了除了生产率之外更丰富的解释。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人类历史中的几种代表性创新,比如科技、家庭、商业、金融以及国家的价值。如果我们对此作更进一步的思考,把文明定义为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那么也许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也许不仅仅是文明的催化剂或者动力,而就是文明本身。毕竟只有在文明的地方,人际网络合作秩序才可以大幅拓展,才可能诞生上述诸多创新。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