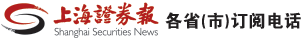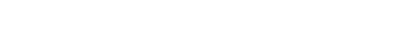从改善就业收入入手 优化促消费政策体系
□ 王允贵
□ 千方百计地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企业是就业和收入的载体,没有繁荣兴盛的企业就不可能有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因此,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所有政策都应围绕企业存活、企业兴旺做文章
□ 深化改革,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建议深入研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路径,包括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保障措施,鼓励和扶助经营性收入,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把股票和债券市场从融资定位转向投资定位,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
□ 加大财政对民生保障项目支出强度,释放消费潜力:直面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底层逻辑,健全民生安全社会保障网
□ 阶段性调降所得税,促进消费和企业利润改善:建议在系统研究所得税改革方案的同时,阶段性调整个人所得税,例如研究实施2年或3年执行期,将最低起征点调升至8000元,累进制最高税率降至30%,让中等收入群体恢复消费信心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9%,美国为82.6%,日本为74.9%,印度为72.3%,韩国为64.3%,比较来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今年上半年,经济稳步恢复,消费复苏加快,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升至77.2%。不过,与疫情发生前相比,总体消费依然偏弱,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8.2%。究其根源,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影响了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
■
就业状况与消费信心密切相关。面对激烈的岗位竞争,居民会增强忧患意识,减低消费,增加储蓄。因此,就业率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变化直接影响消费信心和预期。
1.就业人数亟待增加
2022年我国就业人数为73351万人,同比下降1.7%。就业人数的减少,不但影响失业家庭的消费支出,也增加社会对就业保障的焦虑。事实上,2019年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徘徊在5%。
2.需求端吸收就业能力不足
在失业人口中,青年人失业对消费的压制较为明显。青年人失业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意愿,并对周围人群形成谨慎消费暗示。
3.农民就业转换面临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民工接近3亿人。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较为庞大的就业群体。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农民工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2012年“16—30岁”和“50岁以上”两个组别农民工占比分别为36.8%和15.1%,2022年两个组别占比分别调整至19.8%和29.2%,十年间农民工“老了”很多,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提升了14.1个百分点,30岁以下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房地产等行业加快调整,农民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2022年外出农民工在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就业占比,较2019年分别下降了1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
■
消费不但取决于当期收入,也取决于未来收入,特别是整个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收入。当前消费不振,核心是收入增长放缓,未来不确定性加大,导致消费内生动力不足。
1.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疫情发生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0%和6.5%,低于疫情发生前接近9%的各年增速。收入增长的放缓导致居民明显感觉“挣钱难了”,而未来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确定性支出只能靠自家储蓄应对,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占比已降至2023年二季度的64.8%。
2.私营企业工资收入增长放缓
工资收入属于劳动收入,在收入总额中占据主体地位,2022年占比达到55.8%,工资收入增长情况代表了消费能力的基本盘。然而,近年的趋势是工资收入不但增长放缓,而且结构分化加剧。2020年至2022年全国就业人员工资平均增长7.1%,2023年上半年增长6.8%,远低于2017年至2019年平均9.4%的增长速度。
从结构来看,占就业主体的私营企业工资收入增长缓慢。近3年私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明显,从业人员的工资增速显著下降,2020年和2022年分别同比增长4.6%和3.2%,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平均6.1%和5%增速。
3.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
2020年至2022年,居民家庭收入增速普遍下降,但各层级所受影响存在差异。从全国情况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收入3年复合增长率为5.2%,而2017年至2019年这3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0.1%,下降幅度近50%。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中等偏上20%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从2017年至2019年的8.8%和7%下降到2020年至2022年的5.7%和6.5%,而中等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家庭两个时间段的收入增长率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这种收入组别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镇。农村地区除低收入家庭外,其他各组别两个时间段的收入增速变化不大,而城镇地区除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外,其他四个组别收入在2020年至2022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增速降幅都接近50%,中等偏上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分别下降35%和14%。
各组别家庭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说明,城镇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受疫情影响较大,收入越高的家庭收入增速越是缓慢,而高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是消费群体中最有消费能力和消费升级欲望的人群,他们收入放缓必然影响消费信心及消费市场的整体活跃度。
■
就业增长和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消费的变化折射出收入预期的变化。过去十年我国消费规模快速发展,201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6万亿元,2016年和2019年,先后突破30万亿元、40万亿元,2021年达到44.1万亿元。从增速看,除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3.9%外,其余各年增速均保持在8%以上,年均增速为9.0%。然而,2022年以来,消费增长乏力、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渐成趋势性问题。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恢复乏力
2023年以来,随着经济稳步恢复,消费有所复苏,特别是以住宿餐饮业为代表的接触式消费显著回升,但增速依然不高,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从消费类型看,商品零售同比增长6.8%,餐饮收入增长21.4%,真正带动消费增速提升的不是购物,而是餐饮,消费的主力依然低迷,如家电仅同比增长1%,家具增长3.8%,文体办公和建筑装潢分别减少3.9%和6.7%。
2.居民消费支出谨慎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历次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近年来大额商品(不含购房)支出预期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023年二季度大额商品消费支出预期占比跌至17.7%。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看,2023年以来CPI整体走低,上半年同比上涨0.7%,但已连续6个月下行,6月同比零增长,其中,交通通信类物价从2022年6月8.5%的同比增速持续下跌至2023年6月的-6.5%,居住类物价同比零增长,这类“大件”消费物价走低反映出消费需求疲弱,居民消费支出谨慎,改善型消费意愿不强。
3.提升生活质量类消费意愿不突出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为24.5%,比一季增加1.2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比一季度增加0.1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7.5%,比一季度减少了1.3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消费预期没有明显好转,反倒是在压缩理财投资下存款类储蓄需求进一步扩大。居民未来3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中,教育、医疗、旅游位居前三,而大额商品、购房支出消费意愿降幅度最大,较一季度分别下降1.2和1.3个百分点,反映出居民只想保生活刚需,对提升生活品质类消费意愿不强烈。
■
消费者是完全市场化的微观主体,消费市场几乎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宏观调控手段能够直接触达或干预的抓手不多,往往通过影响“钱袋子”和消费预期来间接影响消费。因此,今年以来,消费并没有如期快速反弹,核心问题是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情况改善程度有待提高。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因此,下半年促消费建议从改善就业情况和增加居民收入入手。
1.千方百计地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
企业是就业和收入的载体,没有繁荣兴盛的企业就不可能有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因此,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所有政策都应围绕企业存活、企业兴旺做文章。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对于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了明确政策要求。建议在总结以往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尽快用法律形式将民营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公平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公平受到产权保护等核心内容予以稳定化,让企业家吃到安全经营、大力发展的法律“定心丸”。
2.深化改革,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向现代化的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在收入分配结构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惠及百姓的指标,2022年我国该指标数据达43%,理论上我国更有能力、更有意愿让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体制机制尚存较大改革空间。建议深入研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路径,包括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保障措施,鼓励和扶助经营性收入,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把股票和债券市场从融资定位转向投资定位,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
3.加大财政对民生保障项目支出强度,释放消费潜力
近年来居民少消费多储蓄倾向越来越突出,2022年新增储蓄存款18万亿元,2023年上半年新增10万亿元,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形势下,储蓄逆势激增,只能说明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因此,对于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居高不下的局面,应直面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底层逻辑,逐渐搬掉压在老百姓消费愿望上的“四座大山”(住房、养老、教育、医疗),健全民生安全社会保障网。
4.阶段性调降所得税,促进消费和企业利润改善
目前,个人所得税中劳动所得高于资本所得,不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不利于消费扩容和升级。建议在系统研究所得税改革方案的同时,阶段性调整个人所得税,例如研究实施2年或3年执行期,将最低起征点调升至8000元,累进制最高税率降至30%,让企业和老百姓休养生息,让中等收入群体恢复消费信心。从博弈论原理看,调降幅度要比较明显且一次到位,以取得市场可置信的预期。同时,建议研究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将企业所得税下降3至5个百分点,减税与增加就业倡导相结合。
(作者系艾利艾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