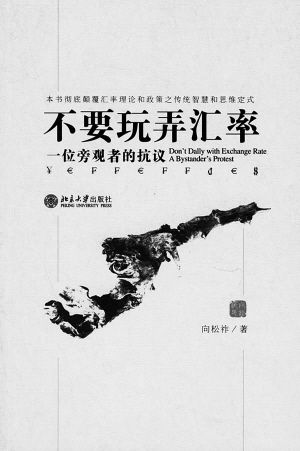|
向松祚先生很谦虚,虽是“欧元之父”蒙代尔的学生,学术上建树颇丰,但他在《不要玩弄汇率》中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旁观者的抗议。我理解他所谓的旁观者,意指是他既不是政府智囊团成员,也不在学术圈。他是华友世纪的董事长,一个商人;所谓商人,在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剔除掉那些浮华的东西,直击核心,而不是陷入利益集团与学院式的派系争斗和口水辩论当中。
他的这一脾性开卷就能感受到,没有引经据典、拉古扯今,而是直接列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十大谬论”,如人民币升值能够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浮动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灵活性等等,然后逐一驳斥。商人最明是非,他的驳斥也甚为“无情”。在提到宋国青利用某贸易条件指标,得出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下降或恶化的结论时,他颇带讽刺口吻道:“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个指标。”
一般的著述,面对这类学术观点的冲突,总要把几个贸易条件列出来,把汇率理论也搬将出来,去伪存真,论个界限分明、一清二楚。可是向松祚却饶有兴趣地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说事:出口价格上升或下降,是商人们的生意决策,取决于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贸易条件恶化或出口价格降低,并不意味着自己吃亏了,更与“贫困性增长”没有因果关系。
或许商人眼中的汇率大抵如此,不管你的头衔如何,也不管你采用的是哪种研究方法,若不能完全阐释真实世界的变化,一切皆是枉然。除了宋国青外,向松祚对弥尔顿·弗里德曼、米德、约翰逊等经济学大师对汇率观的批判也是不依不挠,他把这些人称之为“荒唐的顶级经济学大师”,理由是,他们罔顾事实,把真实的世界设想得太简单了。
浮动汇率支持者将价格与汇率的关系给理想化了,并且漠视了预期、不确定性、各种政治经济金融风险对汇率的重大冲击。这一软肋显然容易被人抓住。向松祚直陈:企业家天天抱怨浮动利率之危害,经济学者却依然重弹汇率浮动优越之老调;“鉴古知今,经济学者必须反躬自省,经济学教科书亦当重写。”
事实上,弗里德曼于2002年 90大寿时,对浮动汇率理念已有所改变,趋向认为任何货币制度都需要有一个“锚”。然而此锚未明,弗老人已西去。不过近年来硝烟弥漫的汇率之争当中,一些原先捍卫浮动汇率的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起那个“锚”来。所谓“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细心的人能体味到,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因为浮动汇率并不能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被动应付汇率动荡的机会成本不可低估。
美国华盛顿卡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最近在《财经》年刊上发表文章称,中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问题是“收收放放”的循环,以行政手段遏制货币和信贷扩张是有限的,且破坏了市场机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腐败,公众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投资决策被政治化。于是他呼吁,中国要想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就需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法治化、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但是在我看来,此市场化非彼市场化,在中国,所谓的市场化汇率机制,恰恰可能是另一种“收收放放”的循环,预期、不确定性等因素无一不会产生逆向的投机激励。
我的一些朋友常感慨,现在的经济学者,少有像弗里德曼、蒙代尔一样,旗帜鲜明表明自己对浮动或固定汇率机制的热爱了。官员型学者考虑到自己话语权重的影响,常含混其辞,这自然有情可缘,一些所谓的汇率问题专家,却也每每就事论事,甚至不时当一下“墙头草”,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从这一层面上看,向松祚“不要玩弄汇率”的书名,或许能给这一群体提个醒:观点可以相左,但屁股不能东坐一把西坐一把。
事实上,政治元素在汇率问题上的掺杂,使得这一经济命题变得非常复杂。向松祚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履行国际承诺、肆意大搞财经赤字和货币扩张,“金本位制如是,布协顿森林体系如是,今日相对稳定之国际货币环境亦如是;应该指责的不是固定汇率制,而是各国某些政治家的不负责任、胆大妄为。”反观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乏盲目政治使命感刺激下的货币政策行为与观点。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说,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汇率不是儿戏,单个人可以不幸福,但你却不能轻率地玩弄汇率而使更多的中国人不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玩弄汇率》虽笔墨轻松而犀利,并且不乏幽默,但它绝不是一本“大话”之作,仍是一本严肃的读物———虽事关政经大局,但也与个人福祉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