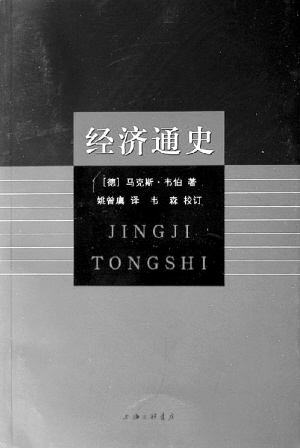|
笔者才疏学浅,长久以来居然不知马克斯·韦伯有《经济通史》一书,要感谢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能让这部著作在中国重见天日。其实这是韦伯作品的第一部中文译本,早在1981年便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付印,当时书名为《世界经济通史》,译者姚曾廙先生。(巧的是,这也是韦伯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著作,译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弗兰克·奈特。)后来才有《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中文译本的问世。后几本大行于市时,坊间《经济通史》早已绝迹。这次韦森教授对老译本重新校订,根据时下的理论知识和学术惯例,更改了一些西方学者的中译名,以及一些专业术语的译法。难能可贵的是,韦森教授甘当校订者,而没有冠之于全新译本,以译者自居。
《经济通史》是韦伯最后一部著作,是根据他1919年至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课程时学生们的听课笔记整理出来的。伊拉·科恩在他的导读中称此书“在所有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的古典先驱中,只有韦伯的这部著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历史分析。”而在其他学者大家那里,相同主题的作品要么是散乱的、缺乏连贯性,要么就是高度抽象,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还有一点很重要,由于是最晚的作品,韦伯有机会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思考都浓缩在其中:“把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一般性认识,与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有名的论述结合起来了。”
虽说是通史,韦伯并不打算一视同仁地介绍各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制度,他毕生的研究就是围绕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展开的,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全书分为四篇三十章,前三篇都在介绍和分析资本主义前、特别是前夕的西方经济社会状况,分别从农业、工矿业和商业三方面进行阐释。在这基础上,按照历史演化的逻辑,自然而然就导出了第四篇———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马克斯·韦伯始终在运用一个自己创造的概念———理性化(或者合理化)。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宗教的、道德的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面前是苍白无力,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只有具备理性计算能力的人才能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生存下来,任何试图超越这一原则的人们,都将付出代价。
在工业企业中,复式记账的广泛采用,使得资本家能够很精确地核算他的成本和收益。“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主义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但要做到这点,必须存在自由市场。原材料、机器、劳动力都能从市场购买,自己的产品又能自由地销售,这样的成本和收益才是可计算的。在庄园制或者行会制度下,生产都是在强迫或者限制的状态下完成的,生产者和所有者都没有动力多生产物品,因为他们并非为了市场而生产。资本主义工厂可就不同了,不面对特定的阶级和人群,而是服务于任何出钱购买的人。
不仅企业要有理性计算精神,现代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决策,都要是理性主义的。韦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的政治:“在中国的旧制度之下,有一个稀疏的官吏的士大夫阶层盘踞于氏族和工商业行会的牢不可破的势力之上。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他根本不懂法律,但却是写文章的好手……事实上,一切都是基于一项巫术性的理论:太后的圣德和官吏的功勋,也就是说文学修养方面的尽美尽善,在平时就可以使万事顺理成章。”而他眼中的“合理的国家”则是:“它的基础是有专长的官吏阶级和合理的法律。”王安石变法曾试图改变科举结构,让具备行政实干能力的人进入官吏队伍,甚至让有才干的吏晋升为官。但这样的努力在政敌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介甫本人也被扣上了小人的帽子。从此内圣就越来越成为中国士大夫们重视的方面,而事功的外王却难以开出来。西方形式主义法律传统发达,因此涌现了大量的法学家。而在儒家传统那里,法律是要服从礼的,董仲舒就主张用春秋大义断狱。直到清末,还有官吏认为寻章摘句判案是俗吏所为,真正的士大夫要凭自己的内在价值修养去理案。不过到了今天,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僵化地按条文量刑。有的法院甚至开发了量刑软件,工作人员只要输入与案情相关的参数,软件就会自动得出量刑标准。判案完全变成了机械行为。
现在问题来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结论上。
韦伯认为新教徒把赚钱当成他们的天职,似乎赚钱本身只是用来接近上帝的途径。我没有在英、美生活过,他们身上是否真有这样的情感,我很难断定。不过他们对工作对事业的虔诚,可能就是从宗教情节中衍生而来的。中国是个彻底世俗的社会,即使有宗教信仰的人,功利色彩大多也十分浓厚。这个特点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国人的内心确实没有什么终极价值,对于普通百姓,福禄寿便是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从不担心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搞不下去,动力一旦释放便是无穷的,不会有价值观上的激烈冲突。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毫无理想的社会,经济为了增长而增长。现在有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复活儒家精神来柔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努力能否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提供精神层面的内容,是历史留给中国学者的大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