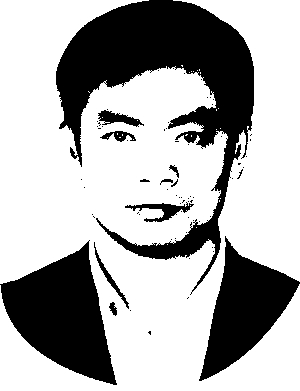|
如果即将到来的技术与产业革命需要5至8年,那么中国大概还有3至5年的追赶期。假如发展方式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章玉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提到如此高度,讨论有如此强度,是今年“两会”的最大看点。笔者相信,只要各级各地政府以及有关市场主体能够拿出转型的具体时间表并将其付诸实际行动,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有望迎来实质性解决的时机。
近30 年来的转型发展史表明,尽管中国民间并不缺乏适应经济转型的自觉性与原动力,但作为转型必备条件之一的执行力,长期以来未有实质性提高;相关的配套条件也很不完善,从而造成各级各地政府对此始终未能形成有效合力;加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延续至今,转型面临的约束瓶颈亦愈渐增强。
终于,这场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领域里长期积累的矛盾提前暴发。政府再次展现出了高水准的反危机能力,相对保守的金融发展与开放理念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躲过了更大规模的危机冲击。看起来,我们暂时获得了相较于美欧和日本的某些经济优势,但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优势究竟能持续多久。事实上,美欧金融业差不多已经止血,经济在迈向复苏通道过程中难免还会遇到一些挫折乃至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有望保持向好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这两年,美欧和日本的核心企业也没有减少对研发的投入,部分跨国公司甚至还大幅增加对前沿科技的研发投入。以埃克森美孚、沃尔玛、通用电气、英特尔、微软、谷歌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仍然是业界寂寞高手;丰田的“召回门”事件虽然大大损伤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声誉,但一向视制造业为国际竞争力关键的日本政府不会让其昔日王牌就此沉沦。而且,从历次大规模经济与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在稳住经济基本面之后,一般都会发动新一轮的技术与产业革命。
如今,面对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竞争力的大幅提高,美国正试图寻找一个能形成较长产业链并能提供巨大就业空间的超级产业,以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历史上,汽车和信息技术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现在,美国准备让新能源产业登场了。因为新能源战略基本符合产业革命所需具备的三个特征,特别是其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汽车和建筑等传统产业链的渗透和延伸,将有可能形成支撑美国下一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产业群。虽然目前尚不能判断,新能源产业能否最终改写世界产业发展地图,但已在该领域积累了可观技术基础的发达国家决不会放弃这次可能拉大与新兴经济体差距的难得机会。而且美欧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难以比拟的。
笔者曾多次说过,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非难事,但大并不等于强。同样,经济增长速度快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要看经济增长质量,看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所起作用的大小。科技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而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才能达到60%。如今,中国在少数科技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这并不能掩盖在整体上仍属于技术引进和模仿国家的事实。尽管在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了中国,中国也正在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但仍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事实上只是披上高科技外衣的传统企业,企业生产工艺或技术只是通过购买、代理等方式获得某项专利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企业本身只是帮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一个生产工具,缺乏必要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大大削弱了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部分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努力,遭到了国外资本重重打压。处于产业分工顶端的跨国公司的意图很简单:就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层次,扼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偏重于生产设备的引进而忽视了隐含性知识与能力的学习,大多数中国产业只是处于一种表面繁荣状态,产业安全现状堪忧。随着沿海地区商务成本的上升以及国内市场的日趋饱和,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国际产业资本有获利回收以及将投资转移至越南、印度等价值“洼地”的趋势。这样,极有可能使得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遭受沉没损失。而且,由于本土企业没有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看起来很强大的中国工业企业极有可能面临“产业空洞化”风险。
因此,站在国际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假如这场技术与产业革命需要5至8年,则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时不我待,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审视发展方式“闯关”的急迫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