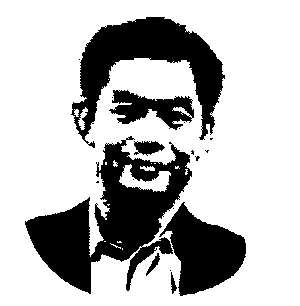|
在人口红利逐趋消失、“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红利逐步递减之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内生性制度红利与市场主体营商禀赋的激发,进而在充分挖掘价值洼地潜能的基础上,打造出能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
在做大经济规模与追求经济增速方面已保持了30余年高水平状态的中国,眼下正面临告别增长偏好、抓紧寻求新增长动力的“时间窗口”。
假如乐观来看,即便既有增长模式不变,至少在未来两三年里,中国应该依然可以做到在世界排名前六的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增速的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明白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所在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以牺牲经济转型时间、拖延深层次改革并导致系统性经济风险上升为显性特征的经济发展思维,最终将恶化本就沉疴难除的中国经济肌体健康。可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近来,西方一些经济观察人士又在弹起了唱衰中国经济前景的老调。例如,总部位于香港的经济研究公司Asianomics的创始人沃尔克(Jim Walker)近日就危言耸听地断言:中国经济崩盘在即!这位研究者悲观地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4%。并坚持认为,对于那些觉得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周期的人来说,他关于中国将发生的通货紧缩的预估将会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当然,沃尔克只是最近10年来看空中国经济的诸多西方学者之一,无论其观点有多耸人听闻,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多新意。不过,换个角度观察,这倒是提醒决策层审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中长期风险的逆耳之言。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以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来看,中国尽管有迥异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特殊国情,亦逐步摸索出了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路径,但作为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余年、且GDP已迈上6万亿美元台阶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不可能总是游离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之外。有人就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依据那样的推论,则本轮平均每年9%以上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更乐观的估计还有:中国仅凭政策操作空间至少可以实现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至2030年。果真如此,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底基的宏观经济学将会发生彻底的范式革命。
只是,如今连最高决策层也已承认,中国既有经济模式已经到了必须大规模升级的“时间窗口”了。如果说,过去30多年里,中国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加上对出口偏好的坚持,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的增长动力,在不断释放的人口红利,以及 “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三大红利驱动下,得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既有资源禀赋下的一种较优化的增长路径,那么,当上述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陆续减退或者由于负效应的不断表达而再难保持原有增长轨道时,中国能拿出什么样的增长动力组合?备受世界瞩目。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新近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也就是说,即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可以享受的人口红利期也就剩下未来两三年了。而且真实世界有时候还未必兑现这种静态假定。
至于“入世”红利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红利,也由于中国在这方面吸收过猛而面临透支的危险。换句话说,中国未来依靠国外市场的扩大而支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越来越不现实,而发达经济体日渐明显的“再工业化”与产业回流现象也在压缩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假如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面临局部性断档危险的判断比较靠谱,在防止由此引发经济较长时期的衰退,显然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迫切难题。
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逐趋消失、“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红利逐步递减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较以往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大环境下,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内生性制度红利与市场主体营商禀赋的激发,进而在充分挖掘国内价值洼地潜能的基础上,结合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增长,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立体化动力格局。
首先,抓紧整固已有并所剩不多的要素红利。一方面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另一方面,宜充分挖掘国内价值洼地的潜能,实现制造业区域布局的梯度转移,力争在中西部地区打造能够比肩东部经济技术水准的产业集群,将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切实发挥出来。
其次,以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尽快释放内生性制度红利,并给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以新的发挥空间。这要求政府在破除关键领域市场垄断的同时,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上述行业的准入门槛。这是一条不可逆的改革路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投资效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最终孕育出一批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超级企业。
最后,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加大对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领域的投资与研发,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力争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以帮助告别旧有增长路径,开启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