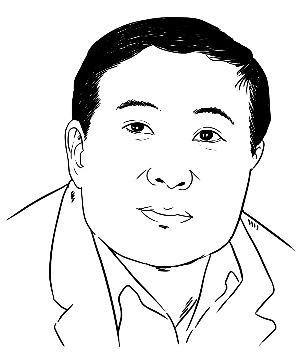|
孙 涤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
探讨经济与社会怎样才能健康地持续发展,自然需要更宏观的时间框架。像期货交易员那样以秒和天为单位,企业投资者那样以季和年为单位,或者政府官员那样以五年为单位,肯定不行。我们考虑的时间,至少要以代为单位。代际的互动,不妨称为“代际抱团”,在现行的体制安排下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困扰。在美国,人们发觉70岁以上的群体所消耗的资源已经超过了20岁以下的群体消耗的两倍。如此抱团,持续成长是可行的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显露出的人口变化新趋势,2002年在联合国人口报告得到“官方”的认定:全球范围的总和生育率(TFR)从2.1下降到了1.85。TFR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数。除了抵补父母的2,这多出的0.1是为了补偿孩子未到生育年龄夭亡的损失,在发展中地区为了补偿较高的婴孩夭折率,这个数大约在0.33;而在人类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直至二十世纪,这个数还在4以上。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规模就趋于缩小。虽然妇女把育龄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会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但女性的生育倾向——TFR的决定因素形成后,再要改变是很艰难的。随之而来一系列的重大变更,对社会经济政策构成的严峻挑战,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人口增长的这个新规律,在中国却是个“新新规律”,不得不多加个“新”字,因为在五十多年前马寅初先生引发的那场大辩论,名为“新人口论”。其实马先生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当年意识形态之争弥漫又有冷战的急迫压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达了,“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中国国情同样适用。
马尔萨斯总结的“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手”的生产仅能维持“口”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很容易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然后“口”的增加必会被饥馑、瘟疫、灾难、战争悲惨地平衡掉。其结果是,人类社会组织经济生产的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惨与牲畜无异。直到1790年前后,欧美国家的物质生产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增长。此前的2500年里,世界的人均生产增加了不过一倍而已,以后的220年则突飞猛进,例如美国的人均生产,提高了竟有四十倍之多。当时中国贫弱,积累低,技术创新基础差,无法迅速把民众的“消费的口”转换成“生产的手”,更谈不上“创新的脑”。这种约束之下,人口过多首先是个拖累,必须有计划地加以节制。可是直到目前,检讨这段历史时人们还在“炒冷饭”,似乎马先生当年争辩的人口政策遭到杯葛,在于它的“新”。
本文的目的之一,则要提请大家注意,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已然明白无误,我们若不能对人口政策及时改弦更张,松绑一胎化的限制,对我们的持续发展将有“釜底抽薪”的危害。
为了增加一些感性的体认,你可描绘这样一个模型:画两根平行直线,形成一个“时间通道”,把每个同龄人群画成一行小人形(每个小人形代表一百万人),比如71岁的同龄人有2800万,就画成28个小人形的一行,同龄5岁的2100人就是21个小人形的一行,如此安排的1380个小人图形,你会对中国人口(13.8亿)的年龄结构一目了然。然后再把15至64岁、低于15岁、高于64岁这三个区间浓淡不同地标示出来,你就很清楚劳动者和他们需要抚养的人口的比例关系了。把人口变化动态化也挺简单的:把时间坐标往下拖就行了,去年n岁的人今年准是n+1岁。加上新生儿的一行,减掉去世的一行,就不难大致再现几个世纪前后、甚至整个历史发生过的人口变迁。
理想的年龄结构当然是纺锤图形,干活的人居多而两头需要抚养的人少。不过这持续不了多久,出生率维持在低水平,图形转眼就会蜕变成为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不过历史上这还确实没发生过。我们不妨把0至100岁(过100的当做百岁)的那一百行的人看做一个同时活着的生命池,注意点放在每年流入池子的新生儿和流出的死亡人数。1750年前流经生命池子的是“稳流”,许多新生命,或流产或夭折过不了门槛,成年后流出又很快,或战乱或饥馑活不到天年。1750年后英国率先的产业革命给人类提供了生机,于是大量新生命汹涌流入。年轻的马尔萨斯洞察到了人口的这个趋势,世称“马氏人口定律”,在其后的世界发展得到印证,长达二百余年,人口的流入湍急(当时全球妇女的TFR在6.0以上)而流出滞缓,生命池犹若尼罗河般泛滥。
然而,今天这一切已完全改观,而且正在走向反面。始料未及的是,过去四十年来生命池流入量缩减得更厉害,人口的增长率竟“悄悄地”从2.1%减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总人口应当在100亿附近。世界人口增长的骤减,不要说马尔萨斯不曾预见、马寅初未能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想到。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生命池里湍流激荡?我们下期接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