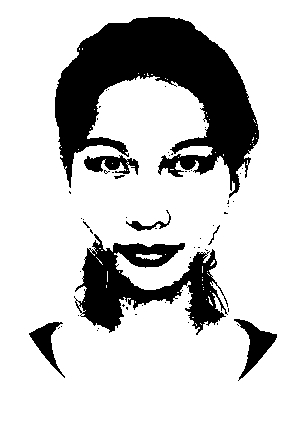|
数字是优化决策的工具,当数字明显偏离常识和现实时,当数据打架时,尤其需要务实的调研和客观的态度。如果我国消费率并没有过低从而投资消费并不存在失衡的判断成立,那么以消费主导拉动经济增长就缺乏前提。为防止发生战略误判,这是不能不辨析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数据打架的时候,更需要务实的调研和客观的态度。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实现投资消费动态平衡的战略转向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任何一种长期形成的慢性病,不可能下猛药求奇效,只能在保持整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通过深层次改革来慢慢恢复健康。
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是投资还是消费的争论中,消费率有没有被低估是个关键性问题。不少人认为,我国消费率被低估了,不存在消费率下降的趋势,主要论据包括灰色支出的存在、服务消费和住房消费支出被低估,以及国际比较方法存在问题。如果我国消费率并没有过低从而投资消费并不存在失衡的判断成立,那么以消费主导拉动经济增长就缺乏前提。为防止发生战略误判,这是不能不辨析清楚的。
第一,灰色支出导致消费率被低估了吗?有人认为,大量灰色消费未能反映在统计数据中,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将个人消费支出计入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导致的消费率被低估和投资率被高估的情况。灰色支出确实存在,但据此还不足以得出消费率被低估的结论,因为国民经济中也存在大量的灰色投资。当一个经济体存在较大的非正规经济和就业时,大量私人消费实际上具有投资属性,比如人们在城市中常见的“黑车”和“摩的”。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被计入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灰色消费”导致“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的逻辑成立,那么“灰色投资”的存在也可能导致“消费率被高估、投资率被低估”。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当一个经济体存在灰色经济时,灰色消费和灰色GDP会产生抵消效应。此外,没有可靠数据说明居民灰色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大于名义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将被漏掉的灰色收入计入后,增量收入带来的增量消费递减,消费支出比重会变小而不是变大,这种情况下消费率甚至存在被高估的可能。
第二,服务消费低估导致消费率被低估了吗?有人以“服务业增加值统计严重缺漏”来反推服务消费支出也存在严重缺漏,但用生产法下的项目来估计支出法下的项目值得商榷,两者更不可对等起来,因为漏掉的产业增加值意味着漏掉了相应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漏掉的服务消费只有在比漏掉的服务产业投资更大的前提下才可能导致消费率被低估。相对重工业,服务业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少,从这方面说服务消费被低估是存在的,但其规模和范围能不能改变消费率整体过低的格局不无疑问。从国际上看,服务业主导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会趋于下降,但我国服务业比重才刚超过第二产业,这一趋势才刚开始。在避免投资率过快下降引起经济失速风险时,比较好的调整方向是,使投资率下降和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上升保持同步。
第三,统计数据中居民住房消费支出过低吗?有人认为统计数据中我国居民住房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4%左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像墨西哥(11%)、土耳其(16.5)和印度的水平(8.6%),是不合理的,应该修正。教育、医疗和住房中的基础部分有公共服务的性质,这些支出会因为各国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同而差别巨大。我国城乡居民年均住房消费支出的数额较小,与住房制度改革直接相关。1998年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后,大量房改房以较低价格作为半福利品卖给城镇职工,较少的住房总支出按折旧率分摊到各年的份额必然也少。从上世纪90年代末住房市场化开始,在城镇化的推动下,住房需求迅速增加,伴随着人均住房面积的提高,房价开始持续上涨。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为20.3平方米,大概可以代表以较小支出取得的住房部分,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2.9平方米,2012年和2000年的面积差,大概是可以用高房价估计支出的相对合理的部分。即使这33平方米的住房都以每平方米4000元-5000元的价格计算,那么每个城镇居民70年的33平方米房屋使用权总价为13.2-16.5万元。从统计数据看,1998年到2012年居民人均住房累积支出为4450元,这个水平确实偏低,但增长的速度很快,平均增长率为9.56%。假设不考虑通胀因素,仍按1998年至2012年人均住房支出的平均增长率计,从1998年至2067年(即70年的房屋使用权存续期),城镇居民人均累计住房支出将超过80万元,这个水平并不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住房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预计还会有较大提升,超过80万元是大概率事件。虽然住房市场化后尤其是2003年以来高房价的问题日益突出,后买房者的住房支出比重越来越高是现实,但并不能以此概括历史的支出水平和总体支出水平,尤其是在我国还有占户籍人口超过60%的农村人口住房支出更低的现实面前。考虑到这些因素,居民住房消费被低估的程度不会太大。
第四,不分发展阶段、不看体制文化差异、不考虑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确实不能作为衡量消费率的有效论据。但是,拉长国际比较的时间和范围,与其他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比较、与同样经历经济体制转轨和文化接近国家的比较、与产业结构发展轨迹相似的国家的比较,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我们把握问题的程度,追溯问题的根源。从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后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率处于较高水平。比如,以现价美元计,在人均GDP达5000至6000美元时,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比美国低了33.4和28.6个百分点,比韩国低了16.5和18.1个百分点,比俄罗斯低了18.8和14.9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了11.2和14.9个百分点,相应的投资率则比这些国家分别高了29.3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28.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
数字是优化决策的工具。当数字明显偏离常识和现实时,当数据打架的时候,更需要务实的调研和客观的态度。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实现投资消费动态平衡的战略转向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任何一种长期形成的慢性病,指望通过下猛药见奇效是异想天开,只有在保持整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通过深层次改革来慢慢恢复健康。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