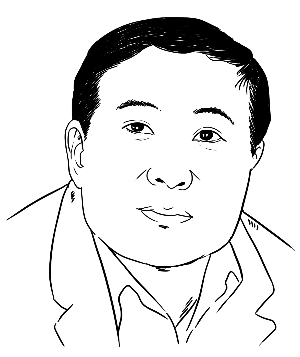|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八十二
□孙 涤
只要寻租和收租方便之门洞开,公务员得以滥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人们本能的贪欲就会不受节制地膨胀,官场就成了陷人入罪的大染缸,不可胜计的人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激发国民道义情感,建立问责体制,先进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取法。
本栏上期以预期效用来计算贪腐的“效益”,得出了荒唐的结果。其所以荒唐,不在于它遵循还是违背了自利最大化的理性原则,而在于背离了人类千万年来合作竞争积淀下来的道义情感的底线,违反了人的良知——根植于人类内心的合作规则。因为贪污就是犯罪!人们憎恶贪腐的道义情感而非理性计算,是希望所在。
人们有权问责官员,他们负有更高的正当性义务。与偶尔到芝加哥大学的访客不同,贝克教授对维持校园秩序理应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道义责任;同理,官员们也该比一般民众尽更大的责任维护公权力,否则应招致更严厉的责罚。笔者以贝氏方法为例证,完全没有贬低教授人格的意思。正如在芝大完成博士学位的好友文贯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年芝大校园仍旧秩序井然,很少有违规乱泊车的现象,可见大多数人还是把“外部效应”看得很重,并没采用贝氏的理性计算法。而很多行为科学实验也证实,常人的良知普遍存在,即使偶尔出格,也是很有限度的。
有个实验是这样来进行的,让被测试者在5分钟内速算20门加减题,设计难度是平均只能做对6题,然后按答对的题数给予奖励,如做对一题给1元钱。结果发现,让被试自报答对的题数时,他们声称答对的题数平均为8,只多虚报了2题左右。当实验确保被试者真实情况无法被验证(如被试能把答卷销毁掉)时,被试的虚报数平均是9题。然而有趣的是,当实验主持人提高奖励,譬如答对一题奖励增加为2、3、5……元,虚报数并没有随之增加。当奖励金额增至15元时,虚报数甚至略有回落,回到了2题左右。实验者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内心自有一杆秤。即使都有“胳膊朝里弯”的自利之心,也是适可而止,“打打擦边球”而已。这杆秤,就是人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道德意识”,在中国话里常常被描述为“良知”。只是这种“良知”与“市场理性”所预期的并不总能合拍。
为什么官员哪怕是职级相当低,短时间内能敛得千万巨资?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视为就业首选,一个初级职位往往有数千人艳羡而争相竞聘? M级、G级贪污的诱惑,超过了常人一辈子(甚至几十辈子)的收入,令固有的“良知”为之夭折。所以说,若把对不正当行为的道义反感摒弃在“理性计算”之外,纯然用狭义的自利最大化原则来计较孰利孰弊,不但反贪无望,官员们不可能“得救”,贪腐的规模只会有增无减。
我有个亲身感悟,也许可用来佐证此理。200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深圳发展银行服务,加班后返回时已近午夜。半路上突感肚子绞痛,急欲上洗手间,赶忙回到住处——在罗湖银行总部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租赁的单居室,却发觉早晨出门钥匙忘在了屋内。强忍腹痛我只得求助门卫。请他们帮着找锁匠。锁匠在半夜被吵醒,把上门服务的费用加倍成两百块,不过倒是二十分钟内就赶到了。那二十分钟真要我的命,锁匠见我形状狼狈,立即作业,不到十秒钟门锁竟然就被打开,令我惊讶不置,顿时不觉得肚子疼了。10秒钟劳动难道值两百元?锁匠颇有些尴尬,生怕我不愿付账,我忙说账自然照付,只是这锁怎么这样不顶用,一面看着那把构造看来相当复杂的房门钥匙。锁匠对我解释,锁本来就只防君子的嘛,开锁看起来费手脚,是为了使客户们看了觉得我们的服务还物有所值。不过话说回来,锁并不是没用。世上一百个人,两个人不需要防,他们说什么也不会偷;两个人防也没用,不管用什么锁,他们也要偷;不过对余下的九十六个,加没加锁、锁难开不难开,可就不一样了。
这话对我不啻醍醐灌顶。我在银行服务多年,参与风险管控的作业,从风险测算、流程设计、奖惩机制,到信息系统建设,做了不少事也读了许多书,从来没遇到过像锁匠那两分钟的开导这么生动那般透彻的,为此我甚至愿意多付他两千块!
孔夫子曾把人分为贤、愚、不肖。贤人从来是极少数,像锁匠口里永远不会便宜行事的两位,即使在孔子的一百三十几位及门弟子里怕也只颜回一人而已。大多数愚人,包括你我在内,是在“与时俱进”的。若是锁不灵光,九十六个“愚人”将不断加入到无论如何都会偷盗的那两个不肖分子的阵列。也许,在瑞典、丹麦那样风尚廉正的国度,只有三、五个人会堕入到不肖分子行列;在希腊、意大利等风纪松弛的国家,有八、九个人会堕入;要是二、三十个已堕入,还有更多人等着要加入此行列,局面就行将失控。这时需要关注的,自然不止是锁灵不灵光,是否得多加把锁,或者加重惩罚力度之类非关键的举措,而是不得不同时关注贪腐的“成果”为什么是如此之诱人,催人前赴后继舍身亡命?要知道,内有金库时,门边多加一道锁是无济于事的。
接着继续追问,究竟是谁在设立关卡,让公务员得以滥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从而洞开寻租和收租方便之门?在权利无当,人们本能的贪欲不受节制地膨胀,官场就成了陷人入罪的大染缸,不可胜计的人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样的两败格局不断衰败国家的治理,瓦解公民的合作,致使公共秩序耗散崩溃。
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成功走出家族和氏族的藩篱,步入中央集权国家。然而自秦始皇以来,始终没能再更上层楼,不能有效制约皇权,使之对国家及国民负责。贪腐的泛滥,于是周而复始时不时地发作。所幸,怎样激发出国民的道义情感,如何建立起问责的体制,在克服类似难题上其他先进国家还是有许多经验值得取法的。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