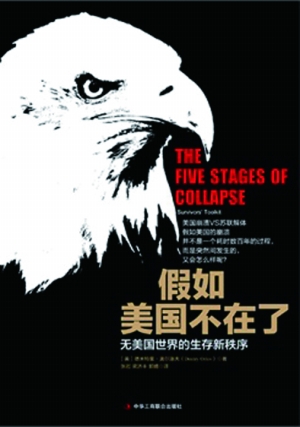|
⊙胡飞雪
德米特里·奥尔洛夫出生在前苏联,少年时移民美国,他的《假如美国不在了——无美国世界的生存新秩序》,既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更有独立学者的胆识,对当今美欧发达经济社会种种问题的描述、解剖和诊断别有一功,尤其对当今美欧发达经济社会未来演变趋势的研判及大崩溃局面出现后的几点建言,值得细细咀嚼。
在悲观论者看来,崩溃意味着世界末日,灾难临头,幸存者们四散奔逃,变成与世隔绝的野蛮人。在理乐观论者看来,人类社会在直线前进,发展、进步是必然的,即使有调整与曲折,也是暂时的、微观的。《假如美国不在了》的基调显然与上述两派都不同,奥尔洛夫悲观却不失理性,他认为崩溃恰好是最恰当的调整,更有效的策略就是把崩溃当作系统设计的过渡期;只要人们转变工作生活方式,奉行极简主义,就仍能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
奥尔洛夫在将人应对和接受悲痛和灾难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的库伯勒——罗斯模型的基础上,设计、描述、推演他的崩溃路线五部曲:金融大崩溃、商业大崩溃、政治大崩溃、社会大崩溃、文化大崩溃。
大崩溃第一部曲是金融大崩溃。奥尔洛夫认为,“延长”和“假装”两个词能很好地概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应对策略:延长政府支持的贷款担保期限,假装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卢森堡前首相、欧元集团主席,也是欧洲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让·克洛德·容克的一句名言最为典型:“当形势变得严峻时,你不得不撒谎。”很多有识之士都说过意思近同的话,如索罗斯就说过:“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在奥尔洛夫看来,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手段是神秘化、故弄玄虚和催眠术。对大多数不明就里的人来说,金融最神秘之处就是创造货币的神圣仪式,专家们摆弄些没有几个人能看懂的数学方程式,而能理解这些方程式的含义并且了解它们与现实世界对应关系的人更少之又少。金融的核心方程式就是债务随着时间推移而呈指数型增长,这就像是安置在所有现代金融架构里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现代金融体系还有一个法宝,即叠加一系列看似很能说明问题其实根本没切中要害的信息来构成假说。现代金融能这样做,又是因为人们会自发地为一些根本无法解释的事寻求解释,并努力从杂乱的信息中提取“合乎情理”的信息。
大崩溃的第二部曲是商业大崩溃,是陌生人之间脆弱的商业信任的丧失。
由于哥伦布及其他航海家、征服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努力,地球大部分地区最终落入了有组织、装备精良的西方殖民者手中,一切以他们的需求为中心,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然变成了商业活动,而贸易、纳贡和物物交换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远在世界另一端的陌生人。工业文明之前通行的人类文明常规恰恰就做了个标准的倒立,现在的人们成了真正的倒立者。这个对倒立的经济形态习以为常的时期注定不会长久,因为这是一个根本上存在缺陷的模式,只有在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持续增长的短暂历史时期内才会行得通。除自然资源不支持西方工业文明永久持续外,奥尔洛夫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陌生人经济贸易的不可持久:人类的进化特征显示,在心理上人们亲近的人一般有12个左右,乐观估计,还有100个左右的朋友、熟人、合作伙伴,一些我们认识且比较信任的人。这是人与人交往的正常模式,是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特质。
大崩溃的第三部曲是政治大崩溃,是政府破产、国家失败、社会动荡。在奥尔洛夫看来,这种政治大崩溃并非一场意外事故,而是工程产物。设计并建造它的工程师包括那些政治科学家,他们试图用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军事霸权来代替有限性战争以实现世界和平。那些经济学家不计一切代价追求稳定和发展,不允许经济出现自然波动。那些金融家,在发生金字塔式骗局时,不是让骗局自然而然地崩塌,而是坚持政府应为其担保。政治大崩溃还是国家过度规模化的结果,推动这辆巨型战车向前的是政客们对权力的渴望。这辆战车的那些权欲熏心的驾驶员们有个特别的盲点:无法认清一个事实——扩张超过了一定规模,只会削弱他们的权力。
政治大崩溃还意味着个人常常处于尴尬境地:互联网的好处显而易见,其坏处却隐藏不露,杀伤力惊人。你上了网,会马上暴露行迹;而假如你时而上网,时而不上网,那就会被监视者认定为形迹可疑,会招来更严密的监视。所以奥尔洛夫给读者提了个建议:学会不通过电子媒介同人打交道的技巧。
大崩溃的第四部曲是社会大崩溃。据奥尔洛夫的描述,在前崩溃阶段,人们在可笑又顽固地推进“逆天的事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不遗余力地破坏社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退化成单纯的商业关系——客户-服务人员模式。教育也与培养文理兼备、学识渊博的人的最高境界越来越远,以至于社会上功能性文盲的比例高达50%。同时慈善也被扭曲异化,成了强加于人的伪善,成了统治体系的一部分。
诊断对了病因,未必能开出有效有价值的药方。奥尔洛夫的办法是倡导罗姆人即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暗示在社会大崩溃后,人们可以罗姆人为榜样模范,这有点矫枉过正了。吉普赛人拒绝与其他群体融合,这样的活法是不值得效法的。
大崩溃第五部曲是文化大崩溃,即人们失去了“善良慷慨、体贴、亲切、诚实、好客、热情和慈善”的能力。家庭成员各自为政,以个人为单位竞争稀缺的资源。作者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大崩溃,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叙述社会学家特恩布尔在《山野之民》中对非洲乌干达北部伊克人的观察。伊克人精明、有进取心、讲求实际且不会感情用事,靠运气和智慧生存。成年男女(其实是青少年)的结合很随便,而离婚、分开也很容易,谁都可以随时抛开对方;孩子在三、四岁时就被推出门外,去自寻野食果蔬,而其老人将死之时,孩子们只以冷眼嘲笑相对,并感到高兴。他们“没有脾气。冷血无情,只求自己能活下去,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臧否祸福”。
可能是由于对人性太过失望悲观的缘故,作者把伊克人把三、四岁的孩子推出门外与发达文明社会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学校相提并论,颇为失当。当然,书中失当甚而谬误之处还有很多,如他说政治阶层、金融精英、行业联合会、产业主、企业主,还有律师,会在每个紧要关口不遗余力地阻挠变革,普通大众不会成为重大变革的障碍,而事实是,谁都可能成为变革的反对者,区别仅仅在于,有人反对无利于自己的变革,有人反对有害于自己的变革,有人反对有利于别人的变革,有人反对有利于自己的变革。
抛开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的世纪末情绪,奥尔洛夫对当今人类社会种种疾患的诊断基本上是准确的。他劝诫人们放弃消费主义,摆脱物欲束缚,提倡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值得世人深思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