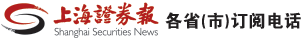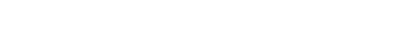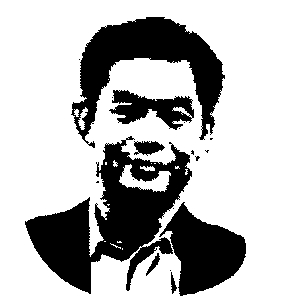营造支持经济创造性跨越的全新生态环境
|
当下,全球科技的发展正在发生不以政府规划为指标参照的变化。中国经济下一个有效增长周期能否如期到来,既取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层面取得的成效,也有赖于微观市场主体创新禀赋的广泛激活,更离不开有效的政府规制与中国社会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的全面释放,以尽快形成催生创新行为所需要的敢于冒险与挑战权威的创新性思维。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蕴藏在无数微观个体中的营商禀赋与创新冲动激活,以早日形成高端产业群。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领衔推出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日前发布,这项指数涵盖了82项具体评估指标,核心部分包括全球各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结果。在该排行榜中,我国首次入选前25位,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排名最高。尤其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知识型员工、15岁青少年能力(阅读、数学与科学)评估、公司培训等10项指标中更位居全球首位;此外,在全球性公司研发投入、知识与技术产出、无形资产等方面,我国的表现亦相对抢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评价我国经济创新能力时表示,中国跻身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前25强,标志着中等收入国家在创新力方面首次加入了高度发达经济体行列。
笔者当然并不认为WIPO这种主要依赖调查取得的数据排名有多大精确性,亦不认同据此指数排名中国创新力就已迈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判断。WIPO的创新指数排名,至多只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这些年在经济制度改进与技术领域进步取得相关成就的一个视角。此外,从更宏观的国际比较视角观察,瑞士连续六年稳居全球创新指数榜首,以及像新加坡、韩国这类中小型经济体位列全球创新指数前列,主要体现的不是多大的战略价值,而是其示范意义。毕竟,今天全球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源动力依然分布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表现,才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与科技格局的变迁。
毫无疑问,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取得的创新成就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忽视的。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取得的系统性进步,本身也是全球创新能力提高的内在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各类公司在全球性研发投入方面的突飞猛进,在知识与技术产出以及无形资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就与我国这些年来在基础性知识与应用技术领域逐步加大投入,以及在知识产权领域从观念到实质性保护同步提高分不开。
最近几年来,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显著加大,素来薄弱的原创能力大大提升,相关科研成果陆续表达出来,甚至出现了井喷趋势,局部领域的企业创新活力显著增强。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超过了日本,去年的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4万亿元。中国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大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2.1%,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高温超导、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热休克蛋白90α、CIPS干细胞等重大突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方面,我国在新一代高速铁路、核电、生物医药等方面也相继取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就在日前,我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如果能够取得后续实验成功,将使我国跻身全球新一代通信网络的领军者行列。
当然,对中国这样的赶超型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局部领域取得的世界级技术进步并非新鲜事儿。客观而言,我国依然是整体技术相对落后、技术之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在全国分布显著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当下全球科技的发展正在发生不以政府规划为指标参照的变化,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以及现在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性企业,在跨产业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对人类未来消费体验的前瞻性研发和测试,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而我国尽管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后续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土地、资源、水和空气质量等因素约束正越来越大,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以及充裕人力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淡出,中国必须尽快形成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质量为支撑的新格局。只是,上述有效增长格局,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亦尚未真正形成。
高科技突破,雄心勃勃的上海被寄予了厚望。但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具符号意义的上海,要想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结合已有“四个中心”的目标建设,进而成为能与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并驾齐驱的最具竞争力城市,需要解决的相关约束瓶颈实在太多,包括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服务意识,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创新性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创新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等等。
上海尚且如此,其他省(市)需要补的课自然就更多了。这些年来,各级各地政府有关支持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的措施不胜枚举,不少规划均瞄准了“世界一流”,目标可谓相当宏大,但真正落实到微观层面的则往往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相背离。中国顶尖高校与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级名校的真正差距,概而言之,就是缺乏孕育一流科研成果所需要的“积极不干预”的科研氛围。另一方面,正如苹果、谷歌以及中国的华为从来都不是政府规划的产物一样,政府不要指望能复制上述企业,政府所关注的,更应该是如何做好幕后的服务,创造更适宜创新的法律和生态环境。
中国经济下一个有效增长周期能否如期到来,既取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层面取得的成效,也有赖于微观市场主体创新禀赋的广泛激活,更离不开有效的政府规制与中国社会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的全面释放,以尽快形成催生创新行为所需要的敢于冒险与挑战权威的创新性思维。换句话说,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蕴藏在无数微观个体中的营商禀赋与创新冲动激活,进一步优化产业配套环境,以早日形成能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进而形成支撑经济创造性跨越的创新生态环境。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