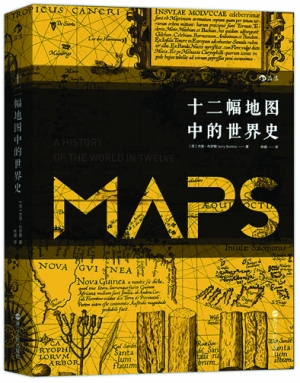3000年人类视野与观念变迁的最直观评注
| ||
|
——读《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严杰夫
2012年底,我在土耳其旅行时曾在加里波利港口短暂停留。这座小港口面朝大海的地方矗立着奥斯曼帝国著名海军将领、地图绘制师皮瑞·雷斯(Piri Reis)的塑像。皮瑞·雷斯一生中最神奇之处就是制作了地图史上那幅著名的“雷斯地图”。后世学者惊呼,这幅制作于16世纪的地图第一次把南极、美洲等新大陆呈现了出来,其精确度堪比现代地图。不过,后来也有许多学者质疑,“雷斯地图”里描绘的并不是南极和美洲,而是部分亚洲和非洲地区。
“雷斯地图”之谜并不是地图史上唯一的未解之谜。前两年,英国历史学家家加文·孟席斯宣称发现的那幅“郑和1418年地图”也曾引起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争论。尽管最后这幅地图被大部分专家鉴定为“赝品”,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地图史领域研究的风云诡谲。
地图作为地理信息载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同样也展现了人类对自身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约翰·布莱恩·哈雷和大卫·伍德沃德合编的《地图学史》,就将地图定义为一种“图像表达”,帮助人们以空间方式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
所以,在以哈雷为代表的这类现代地理学家看来,地图不仅仅只是启蒙时代学者们所认为的“地形关系模型”,还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社会结构的评注”。这样来看,在我们眼前铺开的一幅小小地图,呈现出的信息比想象的要丰富许多。英国历史学家杰里·布罗顿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就借助不同历史时期的十二幅世界地图,串起了人类3000年文明史。这似乎正是地图作为“人类历史评注”的最佳佐证。
布罗顿挑选的这十二幅地图,均匀、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其中包括:公元150年左右诞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1300年左右诞生于意大利奥尔维耶托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16世纪中叶杰拉杜斯·麦卡托绘制的《世界地图》;20世纪出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谈到的那些世界地图;以及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谷歌地球等地图史上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
对大部分人来说,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是这些作品里最出名的一件。它与亚历山大这座城市一起,代表了晚期古希腊文明所达到的高峰。布罗顿强调,正是在托勒密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现代制图术呱呱坠地。不过,布罗顿也指出,尽管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可能是制图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在这部作品里却并不一定包含有地图,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地图。这可能意味着在人类文明的摇篮时期,地理学可能并不占据独立的位置。
希腊地理学最早诞生于有关宇宙起源和创世的哲学与科学思考之中,也因此,我们很难将托勒密的地理学思考放置在纯粹的制图史中去考量,在本质上它属于希腊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在今天,我们会更多将托勒密视作地理学家,但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托勒密可能更多被视为数学家、天文学家,甚至哲学家。
托勒密对宇宙、地理和人类的思考,是在对人类和世界秩序观察和探寻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也是晚期希腊文明放射出的最耀眼光芒。它不仅投射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还穿越千年,为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一缕微弱的烛光。
正如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一样,在启蒙运动时代之前的人类历史中,表达人类与神、与宇宙、与世界的思考,始终都是地图最重要的功能。例如,12世纪制作的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上,就有依照《古兰经》经文绘制的带有火焰般金色光环的边框;而属于基督教世界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也同样展现了十三世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是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宇宙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动物学和人种学信念的反思和再现”。
这些经院式的哲学思考,在中世纪前的世界地图里比比皆是,也成为这些地图中的鲜明特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有关国家、民族、政治、贸易等代表意识形态的要素,取代神学思考和哲学迷思成了地图里最常出现和表达的元素。
不用说,约翰·布劳雄心勃勃想要制作却未能完成的《大地图集》,潜藏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17至18世纪,卡西尼家族制作的《卡西尼地图》则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一幅地图、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共享同样的一套习俗、信仰和传统。”它隐喻着民族主义正取代古代宗教,成为人类的新“神祗”;到了19世纪末,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更将地缘政治的思考注入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术之中。在很多场合,地图和制图术越来越成为人类争夺和宣称财富和权力的工具。
1973年5月,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公布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是以他所谓的“彼得斯投影法”绘制。他声称,他这幅世界地图将取代称霸了地理学界400年的麦卡托1569年投影法。彼得斯之所以要推出新投影法,并非为了创新制图方式和推动地理学研究,而在于抨击麦卡托投影法背后体现出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并推动“平等”对待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他认为,传统的麦卡托投影法将欧洲置于地图中心,导致欧洲和“发达”世界面积不恰当地增大,“第三世界”的面积缩小,尤以非洲和南美洲为甚。而他创设的投影法是“等积”的,可精确地保持国家和大陆“正确”尺寸。
彼得斯投影法体现出的激进观念,迎合了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思潮,在后来的20年中,彼得斯地图成为“史上最流行、最畅销的世界地图”。然而,学术界却对彼得斯的“创新”怀抱恐惧和蔑视,他们直指彼得斯的投影法对基本地图投影原理缺乏基本了解,很难称得上精确,甚至有学者将其斥为“一场出色的诡辩和制图诈骗”。
彼得斯投影法最终使人类社会对地理和地图的理解出现了历史上罕有的大撕裂。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里,布罗顿并没过多评判彼得斯投影法究竟是否科学,而更关注这场大辩论背后所体现出那个时代特征。布罗顿指出,即使彼得斯的方法疑点重重,并且他的世界地图也的确没有如他所称的那般精确,但却揭示了“一个有关制图术的更重要的真相:所有地图都有意无意的是背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产物”。
在布罗顿看来,彼得斯挑起的这场论争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就因为他看到了人类对地图的观念出现了微妙变化:“十八世纪的人相信制图术能够提供透明、理性及科学客观的世界图像……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种信仰渐渐瓦解,因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则利用地图学,制造具有说服力却又有选择性的地图,目的是使它们各自的世界政治构想正当化。”另外,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间对制图术的认识,也出现了巨大鸿沟,正如一切专业学术领域内的从业人员一样,专业制图师也越来越变得“贵族化”和“精英化”,他们将一般民众看成轻信的乌合之众,认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地图,而很容易就被彼得斯这样的人欺骗。
在书的末尾,布罗顿还将谷歌地球列入他的“地图清单”。在他看来,谷歌地球揭示出了地图长久以来承载的一个重要功能——媒介。不过,对这一“发现”,阿诺·彼得斯的对手、美国地理学家亚瑟·罗宾森居功至伟。他率先提出,“地图只是一条管道,信息通过这条管道从地图制作者传输到使用者那里。”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谷歌地球等产品将罗宾森理念付诸实践并往前推进,开创了地图史的新时代。正如有专家评论的那样:谷歌地球“颠倒了作为应用的网络浏览器和作为内容的地图两者扮演的角色,结果产生了一种地图本身成为浏览器的体验”。地图的信息媒介功能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不过,在布罗顿眼中,谷歌地球依旧表明的是“制图师自己的观点”,而并非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所称的那种“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理想中的世界地图。正如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所称“地图非疆域”,谷歌地球最终呈现的也只是其数据库和代码描绘出的景象,与特定地区的现实风貌仍有不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