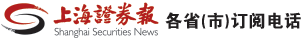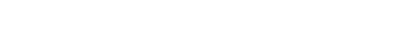中国并未在世界金融发展历程中缺位
| ||
|
——读威廉·戈兹曼《千年金融史》
⊙严杰夫
一般总认为金融是“西方舶来品”,但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不这么看。作为耶鲁大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教授,威廉·戈兹曼对金融史有着独特的看法:“在本质上,金融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像其他技术一样,金融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个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工具。“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之所以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是因为能让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所以,他将时间、机遇和风险、市场,以及法人企业,看成是金融史中永恒的要素。而人类如何去应对及组织这些要素的行为和创新,就构成了金融史的核心内容。很显然,中国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缺位,也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中,戈兹曼以单独章节阐述了中国的金融创新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强调中国的金融史与世界金融史“既是共通的”,又别具一格,“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应对了文明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的挑战”。对比中国和古代西亚及地中海文明的早期金融发展,“即使是硬币、借贷、会计体系、合同、证券甚至纸币等从不同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某些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仍然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均衡点。”
想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去梳理一下中国漫长的历史。
戈兹曼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潮流,发生在商朝。发掘于1976年的河南安阳妇好墓,被视为最有说服力的考古佐证。在妇好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用来陪葬的7000个贝壳。这些看似普通的贝壳,与中国金融史有莫大的关系。
目前已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贝壳曾是早期中国重要的货币形式。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都理解,钱币是用来储藏、计量和转移价值的工具,储存功能要求钱币不易损坏,计量功能要求货币的质量和大小容易以标准单位确认,可转移性则要求货币便于携带。贝壳恰好符合上述所有条件。而且,对当时的商朝来说,这些来自遥远印度洋的贝壳,并非“本地商品”。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贝壳是十分稀缺的,这就保证了货币的供给相对固定。
但随着商王朝实力的壮大,商人控制的区域也迅速扩张。统治区域的扩张,就意味着经济规模的扩张。但贝壳构成的货币却难以跟上经济扩张的节奏。当一个经济体需要更多货币,却无法制造更多贝壳时,商朝在货币形式上就出现了“变革”。考古学者在安阳附近其他商墓中挖掘出了青铜仿制的贝壳。这些铸造的贝壳没有孔,无法用来装饰服饰,考古学家们推断,这些青铜贝壳是新形式的货币。
即使放置到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这些青铜贝壳也是较早出现的金属货币。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白银货币,而地中海地区最早的金属货币为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吕底亚的金银合金小块。这些出现在公元前14至11世纪的商朝青铜贝壳,让中国跻身全球第一批使用金属货币的文明之中。
青铜贝壳开启了中国的金融文明史。而货币成为一条重要主线,也成为中国金融史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金融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商代的青铜贝壳是人类早期金融史中重要的代表的话,那么华夏文明在金融思想史初晓时分就并没有缺席。
戈兹曼出人意料地发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的“金钱观”,即使在今天依旧对我们有许多启示。在代表管仲思想的著作《管子》中,许多章节都展现了管仲为后世留下的丰厚的思想遗产。
在《管子·国蓄》这一章节中,后人记录了管仲与齐王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管仲说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珠玉、黄金、刀币和布币三种货币,既不能够用来取暖,也不能用来充饥,先王是用来控制财务,管理民事,治理天下的。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是很朴素的道理,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货币的工具性。
最难能可贵的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管仲,给予货币的功能性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货币可以用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就是说,在管仲看来,在那个群雄争霸的年代里,货币和法令、军队一样,有着管理国家、抵御外敌的重要作用。同时,管仲还指出,货币不是经济政策的目标,而是媒介。管仲认为,货币就像沟渠一样引导着经济活动,而统治者控制了沟渠,就控制了国家的全部财产。
事实上,正是由于管仲这些独特的思想,为齐国当时的改革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据《史记·货值列传》记载:“(太公)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凭借管仲这些经商济世的独特观念,齐国得以重振,并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目标,可以说完全实现了。
遗憾的是,管仲的这些“金钱观”并未被此后的历代君主所继承,反而是“重农抑商”成为各任统治者所持的主流经济观点。但管仲的货币工具论却成为统治者治邦理国最核心的思想。自管仲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保持经济流通的能力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当然,中国金融史最不能忽视的成就,可能还是要数“交子”的产生。但这却是因为战争。公元993年在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势力一度发展到数十万,并占领了成都城。城内的货币铸造被停止了,并出现了货币短缺。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成都的商人开始自己发行纸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纸币的产生,与商朝青铜贝壳产生的背景异曲同工,都是货币供应上出现了问题以后,人们开始寻求变革和创新,创造出了新形式的货币,以确保经济的正常运行。
李顺起义军的“大蜀”政权存在不足四个月,余部转战各地,不久均遭失败。于是,朝廷开始介入。1005年,成都知府采取措施规范票据(即商人自行发行的纸币),只有16家商号被授予所谓“交子”的垄断印刷权。客户可以在商铺中存下现金,然后获得“交子”,参与交易的商人就可以其作为支付工具代替现金。到了1016年,北宋朝廷进一步撤销了私人印刷纸币的垄断权,将纸币印刷国有化,并于1023年建立了掌管纸币流通印刷的机关——交子务,开始印刷现金准备率为30%的票据。这个交子务看上去很像是今天的中央银行。所以,在宋朝的四川,不仅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似乎还可以说产生了全球央行的雏形。
从商朝的青铜贝壳到管仲时代的“三币”,再到秦始皇时代国家货币体系的建立,以及宋朝纸币的流通,历史的演进勾画出了中国金融史特有的一面。对于中国这一疆域辽阔的国家来说,拥有这样一种源远流长,而又不断地改进和创新的金融传统,是保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基础。所以,戈兹曼才说,尽管“货币对中西方文明来说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说则更加意义重大”。
当然,这种特定的金融文化,也让中国的历史走向与西方有着太大的不同。在戈兹曼看来,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与其说是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等学者解释的由地理因素决定,还不如说是对金融技术使用和态度导致的。
戈兹曼认为,地理决定论的解释忽视了金融在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金融工具和技术的使用始终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个人很难从这些工具的使用中获得太大利益,也因此,这样一种机制尽管维持了中央王朝的稳定,却压抑了金融对个体创新的支持,更不会出现像欧洲那样的资本化趋向。
反观西方世界,19世纪欧洲的金融系统是催生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力。而再往前追溯,更早的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革命,背后也都闪现着意大利银行家们的身影。
这种反差巨大的景象,或许才是造成中西方“大分流”的真正原因。所以,戈兹曼总结说,中国金融技术的独特性,造成它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缺陷。孱弱的欧洲各国政府很早就懂得了发行债券和赤字财政的好处,但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却始终将金融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最终,当清末朝廷财政出现危机时,才从西方“伙伴”那里学会了“债券”和“赤字”,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戈兹曼描绘的这部“千年金融史”,不仅呈现了人类文明各个时期璀璨的金融文化,还为读者呈现了中西方文明在金融领域走出的不同路径,以及各自的优缺点。而最突出的是,戈兹曼将中国独特的金融文明纳入了世界体系之中,并且标出了中国金融史特有的位置。
戈兹曼的独立分析也让我们突然领悟到,在全球携手努力走出“危机”的阴霾之际,东西方的金融文明显然可以贡献出各自不同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