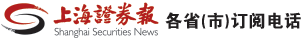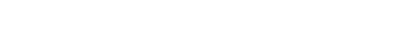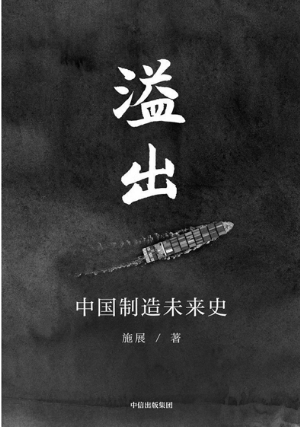“中国制造”为什么不容易被取代——读《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 ||
|
⊙卢扬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发生,网上关于制造业面临严重冲击和向海外转移的担忧增多。自从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样的论调仍不时出现。
研究中国当代战略问题的知名学者、《枢纽》一书的作者施展,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溢出》里,为我们叙述了开启于40余年之前的中国制造业的故事,分析了它自身发展逻辑,勾勒了这种由制造业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商人秩序”,以及它在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故事还得从较远处说起。“多年之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读大学的徐小平站在学校演奏厅里,听到耳边响起那段他已经烂熟于心却始终不知道名字的音乐,还会想起在家乡泰兴镇那个昏暗的夜晚。”在这位现今的著名投资人加入泰兴文工团的第一个春天,他就瞥见了一个拉大提琴的高大身影。在1970年代特有的昏黄灯光下,这个高大身影毫无预兆地闯入了他的心灵世界,他演奏的是贝多芬的《G小调小步舞曲》。这个拉小提琴的人,就是当时担任泰兴文工团指导老师的何彬。他曾是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乐团民乐队的队长,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曲的词作者之一,也是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词作者之一,可算是中国顶级的弦乐演奏家。后来,正是这个人,帮助泰兴成为了世界提琴之都。
40年之后,泰兴下辖的溪桥镇拥有各类提琴生产企业共220多家,年产各类提琴产品70余万把,提琴产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70%,占全世界提琴市场份额的30%。在40年之前,溪桥镇一直就是木匠之乡,很多人都曾在上海学习制作小提琴,后来成立的上海提琴厂里就有不少提琴制作师傅来自溪桥镇。1971年,泰兴县溪桥乐器厂成立了,虽然主要业务仍是给上海提琴厂生产配件,但是厂里的师傅早就有能力生产出一把完整的小提琴了。两年之后,因为何彬的介入,这家乡镇乐器厂生产的提琴终于征服了提琴制作界的专家们,乐器厂获得了生产整琴的资格。一时间,向阳牌提琴享誉全国提琴界。
可惜好景不长。溪桥乐器厂虽然拥有过几年的高光时刻,但它身上的乡镇企业气息一直挥之不去,导致企业规范化管理迟迟难以推进,几乎面临被淘汰的结局。正在此时,一个叫李书的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家企业的走向和命运。在施展笔下,他就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典型。在作者看来,如今人们常常混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职能定位。施展认为,企业家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率先提出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作为企业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者,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从而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就是要不断创造性地破坏既有的经济结构,依靠创新竞争,实现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不过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主导者敢于冒险,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创造出激动人心的新愿景。只有在这时,职业经理人发挥所长的时机到了。因为在完成创造性破坏之后,必须要形成新的规范,才有可能把创新的成果有效地保留下来。这个过程就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参与,这是一个有办法让新规范落地执行的职业。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指五个方面: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新的组织形式。幸运的是,在溪桥乐器厂新任厂长李书身上,这几个特征都能见到。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乐器厂的效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全国行业末尾,攀升到了全国第四。同时,通过抓住政策给予的机会,溪桥乐器厂与上海提琴厂实现了联合,并适时改制成为公司,开始了成规模走出去的历程,最终占据了庞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事实上,这种后发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里。作为亚当·斯密的主要论敌,他批评斯密只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出发,忽视了国家这个贸易的重要中介。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产业政策会经常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这种观点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本书作者认为,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并不是经济中唯一的考量因素,国民经济的自主性同样需要关注,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受阻的时候。具体到微观层面,企业家需要考虑和把握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抓住国家产业政策赋予的机会,在风口结束之前享受到产业政策的红利。
而一个不满足于既有市场、富有远见的企业家,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产业供应链。仍以溪桥乐器厂为例。李书认识到企业的主要目标是需求庞大的中低端市场,只要所有工序能实现标准化,就能迅速量产,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于是,整个泰兴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网络,每一道工序,都有高度专业化的厂家生产,泰兴由此成为了世界提琴之都。
到了1996年,溪桥乐器厂与美国AXL国际乐器有效公司合作,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后来又发展成为凤灵集团,60%的产品都通过AXL公司销往海外。受益于人力成本和优化生产环节能力的优势,凤灵公司不久就击败了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企业,占据了世界中低端提琴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提琴生产企业。由于这种优势地位的存在,他们也逐渐培育出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生态网络。其实,在中国,像溪桥乐器厂这样的企业并不少见,它们虽然在公众中并不具备很高的知名度,但在本行业内,却做成了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这类企业在过去40余年中“野蛮生长”的故事,其实也就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
在施展和他的团队为写本书而赴越南深度考察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费利克斯的越南学者。作者曾经向他请教越南产业链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则颇出乎作者的意料:“我们不需要产业链,我们有广州就行了,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去那里买。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根据作者事后分析,这位越南学者所说的“广州”,也并不是专指广州市,而是指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工业带——那里制造业体系完整,能够提供越南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同时,这位学者也表示,认为越南发展迅猛,未来很可能会超过中国的观点,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为越南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只能期待在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如果这位学者的看法符合真实情况,那么也许至少在中短期之内,中国在国际制造业中的地位仍然稳固。
那么当前制造业的部分转移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书的作者认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这类“转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也就是说,转移的只不过是某些行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而远不是整个生产环节的全部。比如,在组装等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力成本占比高的生产环节,确实发生过转移的现象,但是许多其他生产环节仍很难转移出去,依然保留在中国。其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越多,对中国整个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反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种形式的转移,就是作者所说的“溢出”。
推动中国供应链向东南亚溢出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国民间。近年来国内人工成本增长迅猛,企业家们出于降成本的需要,纷纷把部分生产环节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尤其是越南转移。而从这样成规模的“溢出”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那就是未来世界的经济空间,将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而存在。现实中的国界,已经越来越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其实这种情况早已在上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过,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产业链或供应链的“溢出”和转移。如今,像中国这样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发展中大国,也开始了其供应链部分“溢出”的过程。因此,施展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以国家为唯一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显得无效和无意义了。因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就曾经扮演过推动人类秩序演化的重要作用。尽管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后,商人在人类秩序演进上的作用被边缘化。但是在今天,伴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全球化进程推进,“商人秩序”很可能将找到它的又一次机遇,去主导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