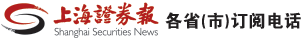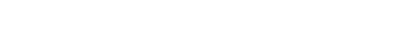世界发展为何如此不均衡——读《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
| ||
|
◎夏学杰
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总是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如果天公不作美,轻则农作物减产,重则颗粒无收。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乃至于狩猎者,都免不了要看大自然的脸色。始于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生存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少,人类开始告别自然的施舍。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就是要探求人类告别施舍之后的世界变迁之原委。格里高利·克拉克,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史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方向为“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国家财富,主要研究对象为英国与印度。
格里高利在书中简单地将人类经济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元1800年以前,一部分是公元1800年以后。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类经济只不过是 “自然”经济,决定生活状况的因素与其他动物如出一辙。它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那个时代,技术进步徒使人口增加,并使生活水准下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工业革命使得人们开始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但随后世界就又陷入大分流时代。因为工业革命一方面缩小了社会内的收入不均,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各社会间的收入差距。全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率先在工业革命时代逃脱陷阱的是英国?随后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
发生工业革命的为什么是1760年人口只有600万的英国,而不是有着3100万人和复杂市场经济的日本,或是拥有2.7亿人口的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认为,在180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在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方面与英国几无差异。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地区在多数方面都与1800年代的西北欧相似。
格里高利给出的解释是,英国的优势不是煤矿、殖民地、宗教改革或是启蒙运动,而是制度稳定和人口的机缘。特别是英国的制度最晚从1200年开始即出奇的稳定,人口在1300年至1760年期间虽然增长缓慢,而富人的繁殖力惊人。基于这些原因,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早嵌入英国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中国和日本在1600年至1800年的走向与英国一致:迈向一个体现勤勉、耐心、诚实、理性、求知欲及学习等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两国也都享有长期制度稳定及私有财产权。但它们走得比英国慢。格里高利表示,中国和日本无法像英国那般一日千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上层社会的生育率仅比大部分人口高一点点。因此两国没有大量受教育阶层的子女向下流动。书中举例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凭他在官僚制度中的位阶就能获得充足的世袭收入。尽管坐拥财富,但他们的生子率仅稍稍超过1(一个父亲生一个儿子)。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主要是因为文化与人口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概括的比较恰当:“工业革命的起因是什么?对这次彻底改变了10万年来人类生活方式的事件,格里高利·克拉克有一个精彩而迷人的解释。”
世界为何出现大分流?
贫富差距始于工业革命,这差不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此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公元元年到公元1400年,全世界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有0.05%。工业革命以后,各国发展差距在逐渐拉大。
格里高利指出,探究过气候、种族、营养、教育和文化等因素的评论家们,皆坚持重复一个论点:贫穷国家缺乏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然而,我们可从两方面证明这个论点显然站不住脚。一是它并未剖析分流的细节,即贫穷国家为何始终贫穷的详尽理由;二是为什么制度与政治改革这两帖药一再失灵,始终无法治愈这些病患。不过,一如前科学时代的医生会用放血来治疗他们不了解的疾病一样,不少现代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如果这帖药治不好病,问题一定是出在剂量不够。
对此,格里高利给出的结论是,效率差异是造成现代经济中国家收入差异的根本因素。自工业革命后,穷国最显著的特色便是生产效率低落。但这个问题并非出在新技术无法流入这些国家,而是穷国无法有效运用这些新的技术。造成各国人均收入出现落差的原因,约有四分之一来自人均实际资本,四分之三来自运用整体投入的效率。在一个资本可轻易在各经济体间流动的世界,资本本身也会与国家效率水准相呼应。效率不彰的国家终会落得资本存量萎缩的下场,效率高的国家则会创造出大量资本。因此效率差异几乎可以用来解释各国收入水准的一切差异。
取得最新技术的难易、规模经济的大小,以及能否适当利用引进的技术,都可能是造成效率差异的因素。效率差异主要是无法有效利用技术所致,其根本在于无法将劳动力有效地运用在生产上,所以就算用最先进的技术,贫穷国家每名工人的产出仍低得可怜。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固然可以转移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各地也能取得物美价廉的生产物资,但支持人们进行生产合作的社会环境却没有那么容易复制。
财富提升人们幸福程度了吗?
英国学者托尼·朱特曾在《沉疴遍地》一书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30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
工业革命引发的财富暴增导致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暴增了吗?格里高利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研究报告中显示,自1950年以来,成功经济体中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并未制造出更大的快乐。以日本为例,从1958年至2004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7倍,但人们自陈的快乐程度却不增反减。这证明了高收入深刻改变了现代发达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财富并没有带来快乐。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如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巨大,但穷国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却只比富国稍微低一点的原因。金钱确实可以买到快乐,但那种快乐是从别人身上转移而来,而非在总体水平上额外增加的。因此,收入对快乐或许没有绝对的影响,甚至连收入最低的族群也一样。在1800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不如现在,但是那时的人可能和当今最富裕国家的人民一样快乐。
对于财富与幸福的关系,近年来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探讨。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大幅改善人的命运吗?》的著名论文。在世界多个国家开展了关于幸福感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全面调查之后,他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1930年凯恩斯做出预测,在一个世纪之内,人均收入将稳定增长,人们的基本需要将得到满足,工作时间不会超过每周15个小时。现在怎样呢?很显然,凯恩斯错了。尽管人均收入确有增长,但人们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明显变短,并且反倒是越来越长。
作者在书中指出,经济史所呈现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是:物质丰富、幼儿死亡率降低、成人寿命增加,以及不平等的消弭,并未让我们比过狩猎采集生活的祖先更快乐。这又是经济学另一项错误的根本假设。
书中还有很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作者在全书开篇中认为,公元1800年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不比公元前10万年的一般民众优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生活品质均毫无进展。石器时代的采集者从事少量工作即可满足物质所需,1800年代的英国人却得拼命一辈子,才能获得起码的舒适,并且一般采集者的饮食和工作生活,远比1800年的英国典型工人丰富多彩,尽管那时英国人的餐桌上多了茶、胡椒和糖等舶来品。所以,这本书读起来颇有些趣味,一位读者在网上评论道:“很少有一部经济学著作能用前10 页的篇幅就把我牢牢吸引住,这部《告别施舍》做到了。”
格里高利运用各个文明的经济史料,从粗略、杂乱甚至偶尔自相矛盾的实证中,梳理了描述人类悠久历史的简明架构,以人和文化的角度向我们解释制度与资源在社会中的合理角色,揭示文化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格里高利在本书的《自序》中坦言,可以预见的是,本书的一些论点将来会被证明为太过简化,或根本就是谬误。有些论点在经济史领域的同僚中也极具争议性,但它们就算出错,也远胜于学术界常犯的刻意模棱两可、堆砌术语且内容空洞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