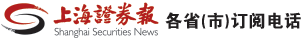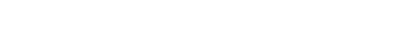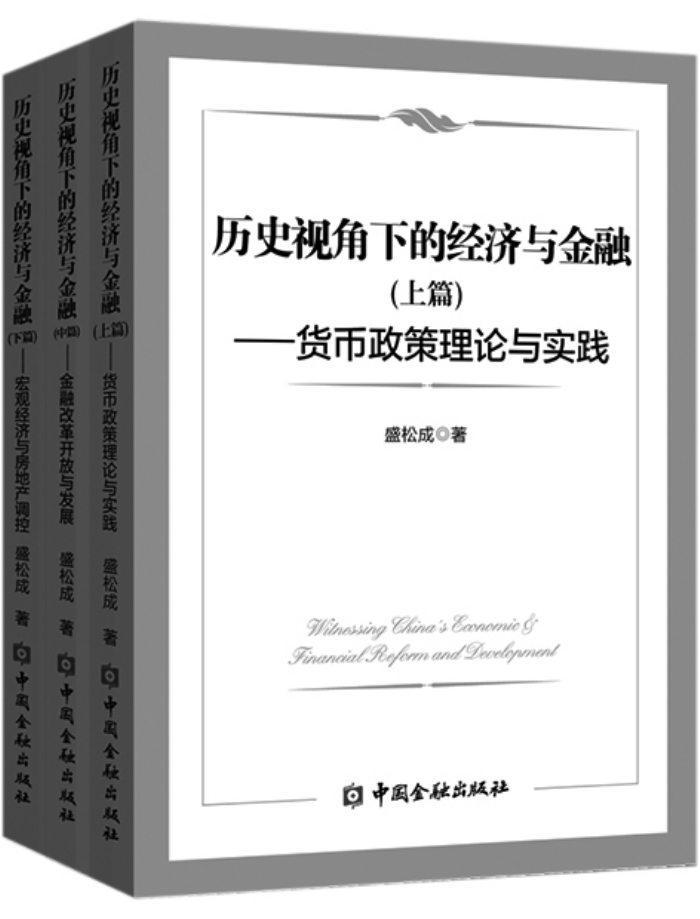从货币学术史研究到货币政策实践——读《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
|
⊙夏斌
盛松成是我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老同事,近期出版的三卷本《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共有14章,约78.6万字,是从其大半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过程中,发表的130多篇文章和采访稿中选取的89篇文章。细细翻阅,可以看出,其在高校从事教学17年和央行工作25年的共计40多年时间里,“一直抱有学术研究的冲动,仍喜欢思考理论问题”的情愫,这主要发轫和得益于攻读硕士、博士生时,师从国内著名教授刘絜敖老先生和胡寄窗老先生的那段时期。可以说,其学术志向的确立,治学方法的讲究,就是在被其称为“人生中最难忘、最充实的美好时光,也是我心态最平静、吸收知识最丰富”的研究生期间铸就的,以至于“至今想来,仍留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平静生活”。本书洋洋几十万字,共计14章丰富的研究内容,不仅体现了松成几十年的研究心路,而且反映了其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当时政策演变背景下进行决策时的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以及学理机理的辨析历程。了解至此,自然不仅对理解货币金融理论在中国当下的运用有益,而且对研究和探索中国经济与金融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也是有益的。受松成之邀,写点书评文字,我顺便借此机,引而开之,谈三点既是对书的评语,也是本人长期从事金融研究工作的感想。
一是嗅觉敏感,问题导向,及时就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新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这是这三卷书的显著特点。松成书中的大多数文章,虽然引述理论,但并不是述而不作,甚至无病呻吟。这些文章往往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直面传统理论的“尴尬”与“苍白”,善于修正理论解释,并能提出适用的政策主张。不管是在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上,还是在比特币、虚拟货币、天枰币和P2P的问题上,松成都能敏锐、及时指地出问题的理论实质,提出鲜明的政策主张。我是长期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在这方面对松成的作为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在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理论创新从操作指标的确立,到正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官方制度的正式确立,松成是功不可没的。
早在我任央行总行非银行司司长,负责整顿全国239家信托公司时隐约感觉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信托公司在过去短短的20年内历史中被五次整顿?到了2006年,我明确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在当年4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发文指出,要正确“把握近年内货币、信贷运行中发生的新情况、新特征”“在企业外源性融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央行的调控更要侧重于企业总体资金面的分析”“要关注银行贷款,更要关注股票、债券、FDI、企业短期融资券和商业票据的发展规模。警惕货币供应偏多,必须规范非银行融资”(夏斌《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上卷》)。但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也就进行到了这一步,在当时只是提出了理论思考。而其后,松成在这个问题上比我有更多的理论阐述,更完整的制度设计思想,并下了更大的功夫在全国推广执行社会融资规模这一客观反映转轨经济货币宏观调控的操作指标,完善了我国经济金融的宏观制度。
二是央行的专家不仅应是货币金融专家,还必须是宏观经济学家。翻阅松成的三卷书,作为一个中央银行的干部,书中内容不仅涉及货币金融理论与实务问题,同时还涉及大量的宏观经济问题。大量的文章发端于金融但又不仅限于金融,而是涉及经济结构、贸易,税收、财政、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企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等多个领域。“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先与‘货币面纱观’决裂,他是将货币因素融入理论经济学的首创者”“凯恩斯学说使货币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松成的文章对各种问题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时会流露出基于魏克塞尔、凯恩斯等理论先驱的宏观分析基础上的框架思路。这正展现出松成对货币经济学说史的娴熟把握,使得他能够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看待每一个金融问题,并且对其他经济领域问题的分析也都置于货币经济学框架下,即在克服“货币面纱观”的偏见下进行分析。这一点,对于宏观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央行的工作人员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也应该是多多提倡的。
三是有力的理论分析必须具备历史和统计学知识支撑。我崇敬熊彼特的治学。其在鸿篇巨作《经济分析史》中反复提到,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掌握历史、统计和理论三门分析技术。我发现,松成几十年来能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不小的成就,与其在读书期间师从刘絜敖、胡寄窗等几位大师,工作后长期埋头研究货币和经济思想史,然后又调任央行调查统计司担任司长的经历有关。因此,后来不管是相关货币供应量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临时碰到社会上关于比特币、货币非国家化理念等各种经济现象与噪声,或是面临中国要不要建立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时,松成都能牢牢把握住货币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石与主线,并在研究中不时透出其对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货币历史的深厚理论分析功底,以及对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特征的充分了解。
由书评出发,在此与更多的读者共勉:我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研究者,要达到如熊彼特大师所说能熟练掌握三门分析技术确实不容易,但起码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这三门分析技术中,如果统计学学术功底较差,可以借助旁人的学术成就,但如果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弱智”,则是经济学研究的大敌。因为在与旁人争辩解释经济现象,选择当下经济政策,或寻找创新理论时,不了解或者混淆古典与新古典、马克思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历史与制度学派,凯恩斯与后凯恩斯学说之间的差别,肯定会从一个思想史学的“弱智”滑向理论的“弱智”,甚至会落入“鸡同鸭讲”的对话场景。从认识论角度看,后人一切新知识的形成,都会在有意无意中受到前人知识的影响。因此,经济科学上的创新如果不明了“旧的”学说的逻辑始点在哪里,说不清楚在“旧的”说法基础上“新的”说法理论自洽又是怎么开始的,那么一切理论创新都将是无从谈起。
(本文作者系原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创始理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