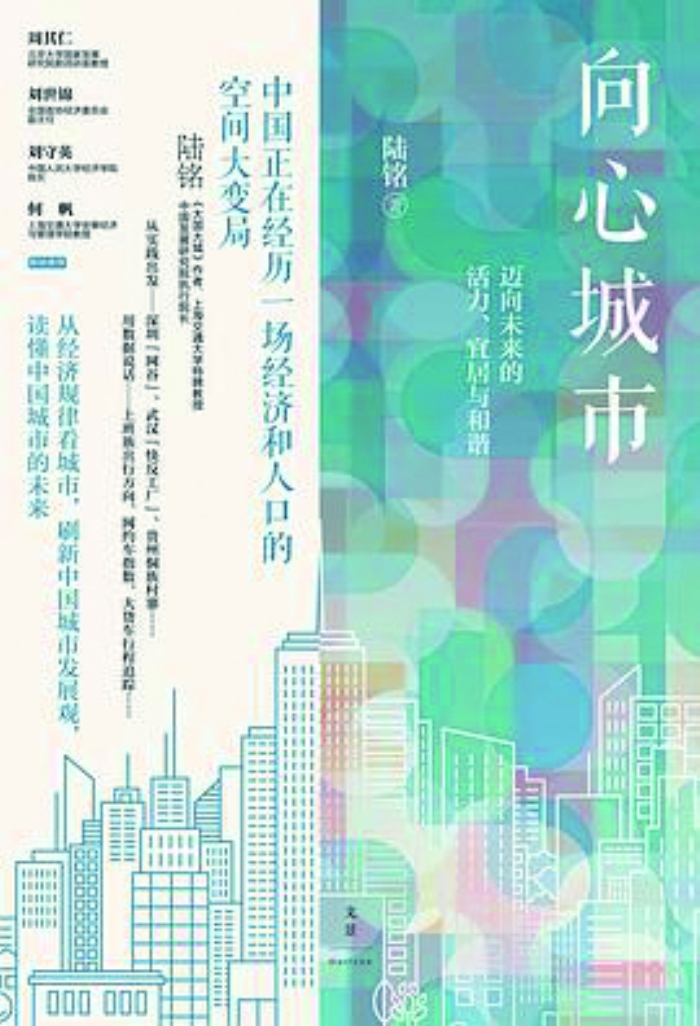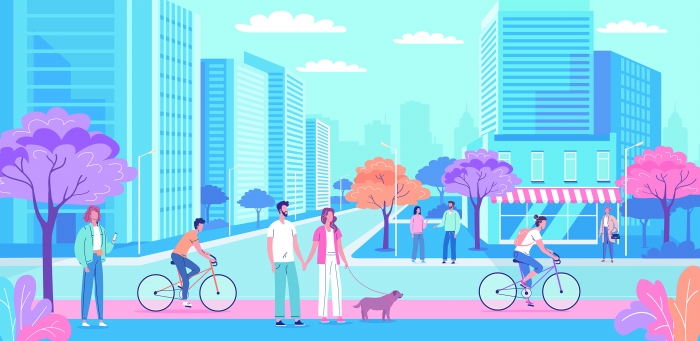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回归以人为本——读《向心城市》
| ||
|
◎徐 瑾
提到城市,总会让我们感慨万千。一方面,城市的便利、活力与机遇,让许多人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城市的高房价、拥挤、污染也让很多人望“城”兴叹。一直以来,“逃离北上广”的声音不绝于耳,“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呼声也层出不穷。真相到底如何?对此,继《大国大城》之后,知名经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其新书《向心城市》中破除了不少城市规划迷思,重新梳理了城市化的诸多问题。
所谓向心城市,其实有三重含义,对应着作者总结的城市发展三大规律。
用动态眼光看待城市化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率往往越高。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指一国之中,有多少比例人口居住在城市。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80%之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在7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横向比较其他国家,中国城市化率还有提升空间,所以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升就不可避免。
作者在书中强调的是,在谈论城市化时应该有动态眼光,要着眼于未来,即明确未来城市为谁服务和以谁为主。因为,主导未来城市的不是60后、70后和80后,而是90后、00后,他们对于城市的期待,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网络理论来看,城市越大越经济。这是因为相同的服务,大城市提供的服务成本更低,并且在环境方面,大城市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更友好。有数据研究表明,一座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与两个各自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相比,虽然人数看起来一样,但是前者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数量要比后者减少15%。
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从日本的案例中得到佐证。日本一直鼓励年轻人离开大城市去小地方生活,但是无论给钱还是给政策,都难以让年轻人从大城市迁离。尽管日本地方议员的政治结构,使各个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有很强大的动力去推出各种地方支援政策,以增加地方人口。比如,从2023年开始,对于搬离东京都市圈的人可以直接奖励现金,每人大约100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5.3万元)。但是问题在于,无论你选择就业还是求学,无论选择结婚还是单身,东京等都市圈的吸引力一直都在,这也是很多人离开大城市最终又回来的原因。
“逆城市化”可能是暂时的
其次,作者在书中指出,从城市人口的分布趋势来看,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而今,在大城市生活的缺点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这些抱怨可以被看见和听见,本身就是大城市话语权更大的体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趋势也许只是暂时的现象,即使在发达国家,虽然曾一度出现过人们远离大城市的情形,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了逆转。作者在书中列举了美国和英国的案例。比如,纽约的人口从1980年的707.16万回升至2000年的800.83万,2010年达到817.51万,2017年达到862万。其中,曼哈顿区的人口则从1980年的142.83万回升到了2000年的153.72万,而2010年达到158.59万,2017年达到166万。伦敦也是如此,内伦敦人口从1981年的249.80万回升至2001年的276.61万,2011年则超过320万。
城市将越来越重要
最后,从不少大城市或都市圈的发展规律来看,在经历了工业化又转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都出现了先从市中心向外分散,然后再向市中心集中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研究结果,将影响未来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制定。这些年来,中国有不少城市都在呼吁提高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的比重。为什么服务业很重要?我们重新反思一下经济,就会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互为因果。
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工资等劳动成本越高,在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就越来越低,而服务业则可以弥补这一短板。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结果也意味着人们收入更高,消费也会更高。更进一步分析,很多服务说到底,又依赖线下的网点提供给消费者。毕竟,服务业与人密切相关,很多时候必须依靠面对面的交流。由于城市越大,规模效应越大,服务业可以更好更深入地发展。很多国家都走过探索和发展服务业这条道路,比如英国曾经为制造业的没落而彷徨,最终却在金融业的崛起中找回自信与定位。作者强调,在后工业时代,城市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服务业,特别是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集聚到中心城区”。
也许这样的表述有点抽象,但你可以从身边的餐桌和自己的胃去思考这个问题。民以食为天,餐饮其实一个城市服务业的观察窗口。我们无须采用米其林等高大上的指标,用更平易近人的数据就可以分析这个问题。在书中,作者就用大众点评网的数据来体现了城市与餐饮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城市人口数量每增加1%,菜品种类就会增加0.528%至0.623%;而且城市“流动人口”比重每上升1%,菜品种类就会增加2.19%至2.49%。菜品种类的增长大概是“流动人口”增长的两倍。这意味着城市越大,外来人口越多,他们不仅带来就业,也带来了消费,尤其是符合自己口味的饮食习惯,进而也丰富了城市原有居民的餐桌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布局也会应运而变。漫步城市,你会发现最核心的城市区域,比如北京的国贸,上海的陆家嘴,以及纽约的曼哈顿等地,往往属于各类商业中心,被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占据,而各类科技公司则处在非市中心区域,而制造业企业则处在更偏远的地区。
要考虑公共服务的可达性
作者指出,这种层式的结构在多数城市都存在,“中心城区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更多、更好、更多样的服务业,以及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不管人们居住在市中心,还是企业的办公地点在市中心,均可以获得更好的便利性,但同时也要付出更高的房价和租金。”因为最市中心的行业和企业,往往最需要与人见面,而博物馆、音乐厅等政府提供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也会规划在城市副中心。制造业之所以多数安置在郊区,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污染,而是因为制造业占地较多,并且也不需要与那么多的人打交道。
更有意思的问题在于,城市发展要以人为本,那么在这样的产业布局下,人去了哪里?作者指出,在一个城市内部的每一个位置上,都会有一些居住用地的布局,夹杂在金融、科技、教育,甚至远郊的制造业用地中间。当然,越靠近市中心,地价就越贵,越靠近郊区,地价就越便宜,而且这种趋势不太会改变,因为去大城市以及住在大城市中心,就意味着你在一个演唱会的前台位置,可以看得更清楚,体验更好,收费也会更贵。也正因为如此,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人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尊重和引用空间结构规律,而不是强行疏散。对此,作者在书中表示,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底层逻辑,政府在规划和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时,既需要适应市场的逻辑,也需要考虑不同地段的公共服务可达性。
总体而言,作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不会改变,甚至城市、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市中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由于人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那么对于个体而言,应该何去何从?对于大城市的居民,需要在房价、收入和通勤之间权衡,选择自己最适合的平衡策略,要么居住在市中心,得到更多资源的同时承受高房价,要么付出更多通勤时间得到更多居住空间,要么索性工作在郊区,放弃高薪收入的同时也规避了高房价的痛苦。这个道理,其实可以推演你到底是想居住在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抑或小地方。其实,没有一个决策绝对是好是坏,而是每个人根据自身的资源以及期待而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发展为了什么?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即一个人如何说不重要,关键是看他如何做。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已成为一种趋势,其中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享受,有的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每一种价值应如何进行具体的界定,不同人的认知并不一致。即便人们对每一种价值的含义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每一个人对于每一种价值所赋予的权重又可能不一样。正是这种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汇聚在一起,在交换中形成了大家的选择,正如作者所言,基于认可多元价值的最优化原则之下,城市治理本质就是“要在城市广泛存在的公共领域中,找到一种机制来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把选择权交给个体,让个体的偏好得到体现,也许是我们城市规划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