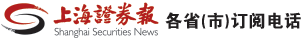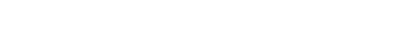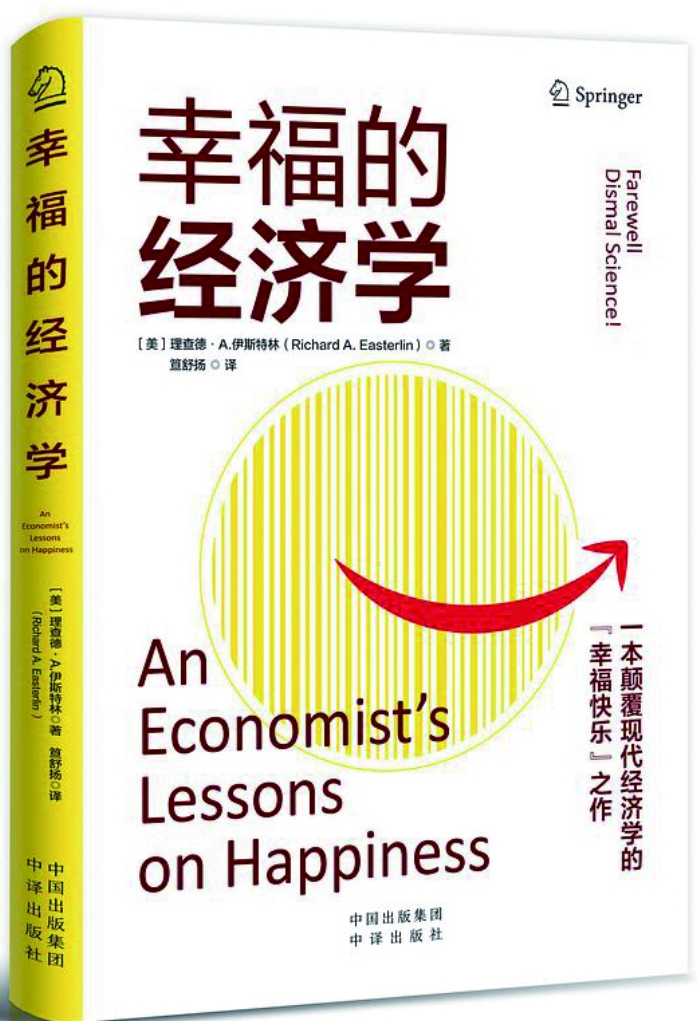经济学能否带来幸福?——读《幸福的经济学》
| ||
|
◎徐 瑾
提到经济学,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与GDP和收入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指标,似乎与有些虚无缥缈的幸福感有些绝缘。其实经济学和幸福的渊源不浅。“幸福经济学”之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其所著的《幸福的经济学》一书中告诉我们,幸福可以度量,而经济学也可以和幸福有关。
经济学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经济学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经济的英文economy就是古希腊语家政术,意味着管理家庭。由此可见,经济学其实一直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幸福是什么?古往今来,从希腊人到现代人都在一直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眼中,“中等水平的财富,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就是幸福”。
早在两百多年前,哲学家穆勒就指出“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是不同极端的幸福,代表着纯粹精神快乐与单纯的身体享乐。到古典经济学时代,“幸福”或者说公共的福祉,在杰里米·边沁等古典经济学者的眼中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看重“效用”,探索人类如何追求美好生活,幸福自然是绕不开的主题。
那么,幸福什么时候开始和经济学脱钩?伊斯特林指出,这发生在20世纪初,与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有关。众所周知,帕累托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从他开始,经济学家与幸福的关系渐行渐远,这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帕累托认为经济学与幸福无关,反而应当关注决策,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而非结果的科学。”
帕累托的思想主宰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研究,这导致直到二战后,幸福经济学才演化为一门社会科学。幸福经济学之所以起步晚,除了受帕累托个人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幸福很难度量。确实,收入可以用货币计量,但是幸福如何度量,却让人犯难,毕竟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它关乎感受,也与性别、年龄、健康等因素都相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关乎收入与德性。在现代,幸福可以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
幸福最终可以被测量要感谢二十世纪兴起的民意调查。虽然这些调查对幸福的定义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大体可以度量出人们的幸福度。伊斯特林曾任美国人口协会、经济史协会和西方国际经济协会主席。作为第一位探究如何度量幸福的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自1970年代就开始使用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他原本是想证明一个常识,就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钱越多就越幸福”,但是结果却发现了幸福-收入悖论,也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
幸福与收入的悖论
幸福-收入悖论到底是什么?想想,如果收入增加,你会更幸福吗?对这个答案,你多半是肯定回答。即使在美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压倒性的肯定,甚至不分行业。不过,伊斯特林指出:“这仅仅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看法,而有时事与愿违。”
幸福-收入悖论源自伊斯特林在1970年代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想搞清楚“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但是结论却出乎预料。伊斯特林有两大发现:一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确实如普通人所想,钱越多越幸福,即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二是伴随着时间的延长,从整体来看,收入的增加并不会伴随着更强烈的幸福感。
总结一下,就是幸福和收入的长期趋势没有系统相关性。比如,美国的数据最完备,但是分析结果显示,在过去的70年里,虽然收入实际上增加两倍,但是大家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对比之下,拉美的经济虽然不如美国,但是幸福指数并不低,尤其是巴西从1990年到2012年,虽然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高,但幸福指数却呈上升趋势。
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最开始只是用了美国数据,随后作者在不同国家交叉对比时也有了新的发现,幸福和收入的悖论关系,不仅在国家内部个体比较时候成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比较也成立。比如,富裕的国家通常比贫穷的国家更幸福,但随着时间变化,幸福和收入关系又不那么明显了,在收入增长更快的国家,幸福感并不会增长得更快。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幸福或者幸福的增加,在收入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快乐或者幸福会随收入而增加,但是当迈过某个临界点后,收入和幸福就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了。
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国民幸福的途径之一,但并非是唯一途径。这在不少转型国家尤其有参考意义。比如,东德与西德的统一发生在1990年10月。按照经济学家的估算,随着两个德国走向市场经济,按道理民众的幸福感应该增加,结果却事与愿违,在德国合并的那一年,出现了幸福指数突然下降,经过二十多年后,幸福感才逐渐恢复。原因在哪里?经济变化是一个首要因素:“从1990年到1991年,产出急剧下降,大约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生活满意度随之崩溃。产出下降的另一面是企业破产所致的大规模失业。”可以说,失业打击是全方面的,不仅影响失业者,也会影响就业者。
伊斯特林研究发现,除了经济因素,原有教育、医疗、住房、工作等社会安全网的瓦解,也是一个核心因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原先政府会解决这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问题,现在都交给了市场,这自然会带来不安。英国劳动力市场分析专家罗杰·卢姆利指出,在东德原本体制下不仅没有失业、没有大的通货膨胀、工作强度低,而且还有免费医疗和社会服务,连住房和公共交通价格都很实惠,但是这些福利在德国统一后都消失了。这使德国东部的许多人产生了幻灭感、不利感和不安全感。当然,随着东西部融合、东部经济快速增长,最终大家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幸福感才逐渐有了回升。
我的幸福在哪里?
幸福,有时关乎比较。比如,有时收入的提升,却没有带来满足感,这是因为当他人的收入增加时,每个人的收入参考水平都会上升,从而削弱了自身收入增加对幸福的积极影响。这一点在低收入国家也不例外。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现实中,人们也都能发现这样一些现象,比如有的人有钱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或者有人没有多少钱也很幸福。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这可能说明一点,有些人的幸福与痛苦的根源和金钱无关,有的人天生也许就更容易快乐,有的人也许就天生不那么容易感受到幸福。
“我的幸福在哪里?”在未来的政策中,幸福经济学也许真如作家萧伯纳所言,“经济学是使人幸福的学问”。也正因如此,伊斯特林呼吁第三次革命,也就是继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之后的幸福革命。前两者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兴起的结果,而他认为幸福革命则是社会科学的产物。这意味着,人们的感受会更重要,希望这是一个经济学更人性化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而言,本书的作者具有先见之明。他很早就指出,常见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等经济指标虽然有用,但是并不能直接作为幸福革命的衡量标准。“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相反,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导致了对工作、收入、医保和家庭环境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当社会变迁的时候,往昔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被打破,这个时候即使经济上升,可能也不足以带来全体社会的幸福感。
按照202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其对幸福的标准涵盖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等多个方面。在全球146个经济体的幸福排名中,芬兰连续第5年被评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丹麦等北欧高福利国家基本都位居前列。
如何提升幸福感并不是幸福经济学唯一目标,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却是了解幸福经济学的动力,也正因如此,谈论幸福,要回到日常点滴。那么如何提升幸福感?从个人角度出发,也许幸福经济还应该考虑个体因素,比如对于幸福感知很可能和个体感受以及基因有关。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应该考虑引入安全网络政策,这也是福利政策逐渐从欧洲走向世界的原因。
关于幸福的研究还在延续,也不断有新的结论出现。这背后,都离不开伊斯特林作为“幸福经济学”奠基人的作用,也离不开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