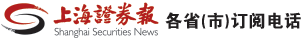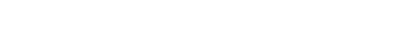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利己”与“利公”的三千年博弈——读《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
| ||
|
◎禾 刀
1776年,经过3年时间的打磨,亚当·斯密出版了后来震惊世人的《国富论》。在这本著作中,斯密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即发现了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无论斯密是否发现,作为人性本能,这只“手”自打人们尝试物质交换时起便已经存在,并不随某个人的意志所转移,只不过它长期遭受社会漠视甚至批判。正因如此,在《国富论》发表前,斯密推出了《道德情操论》,为市场中的自利行为解开了沉重的道德枷锁。
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威廉·马格努森在《逐利而生:3000年公司演变史》中深入剖析了3000年来罗马大税吏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以及脸书等8家极具代表意义的公司。作者认为,从诞生之日起,公司就是一种为促进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机构。但是,作者并没有回避数千年来公司发展存在的短板弊端。他像研究进化论的达尔文那样,将这8家公司逐一分析后发现,每家公司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而如果将这些公司放到时空的纵深,特别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尽管有的公司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功不可没,但公司并不总是自带善良品质,公共政策在规范公司市场行为方面还有更多路要走。
公司与公共利益原本是对好搭档
世界上最早的公司诞生于罗马共和国时期,马格努森从公司单词词根来源角度分析指出,公司一词最初包含“身体”与“合伙”两层意思,前者是个体,后者是整体。也就是说,公司是由多个“身体”通过“合伙”方式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身体”是基础,“合伙”是实现利益的途径。
罗马的大税吏公司是马格努森着重阐述的第一个重要案例。罗马共和国没有形成一个大政府,其“官僚设置始终极为精简,公务人员也非常有限”。人手的捉襟见肘,意味着要完成庞大的治理工作需要有官僚体系之外的力量加以襄助,这便为包括大税吏公司在内的私营公司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于是“罗马共和国授予公司各种特权,公司以服务国家作为回报”,二者进入“你情我愿”的蜜月期。那时的私人公司怎么看都有点像是罗马权力机构的“白手套”。
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特许经营权并不是万能的,尤其在遥远的罗马共和国时代,由于制度尚不健全,在更大利益的驱使下,体量庞大的大税吏公司也在想方设法腐蚀官僚体系。大税吏公司渴望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它们将追求利润放在首位,至于公共利益则被他们抛诸脑后,他们“压迫、残害行省的人民,怂恿新的军事征服;它们冒进求胜使罗马深陷金融危机”。大税吏公司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危及罗马共和国的根基,反噬成为必然,大税吏公司最终走向没落。
大税吏公司确实为罗马政府解决了不少棘手难题,但是他对利益的追求一旦越过红线,必然招致官僚机构的强力反制。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演进,现代国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通过制定诸如《反托拉斯法》等法律约束企业大而难管的行为。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曾提出数十起垄断贸易的诉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1年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裁决,下令解散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这个曾经控制美国90%炼油量、四分之一原油产量的市场巨兽,最终被拆分为34家独立的公司。
马格努森没忘了给那些盲目推崇“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泼冷水。他引用斯密的原话后指出:“斯密没有说追求利益者总是能促进更大的利益,他只是说结果常常如此”。换言之,除了“常常如此”,那么也存在“不常如此”的个案。“常常如此”当然理想,关键在于如何防范“不常如此”的个别现象。
公司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越来越淡
公司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创新史。作者在本书所选择的8家公司,在各个不同时代都有鲜明特色。随着公司这种市场形态的发展完善,公司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创新特色愈发耀眼。在这8家公司中,美第奇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美国的福特公司和KKR私募等4家公司在创新方面可圈可点。
成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银行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银行。现代商业体系或者说许多商业制度的创立离不开中世纪的意大利,而美第奇银行创立的复式记账法,直到今天仍为银行系统沿用。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创新成果之一是股票。虽然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募股早就成为航海家实现融资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先进,他们开创了股权流通的先例。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奔着东南亚胡椒、肉桂和肉豆蔻等香料而来,后来发展到纺织贸易,这却动了英国纺织业的蛋糕,直接导致禁止进口印度印花棉布的《印花棉布法案》出台,显然并不是什么奶酪都可以动的。对英国本土而言,东印度公司创造或者可以说是掠夺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为英国维持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但是,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却与公共利益毫无关联,反而大大损害了当时的清朝和东南亚诸国的利益。
如今,福特公司虽然风光不再,但该公司发明的“水晶宫”流水生产线,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制造企业的标准生产模式。马格努森虽然承认福特的流水线发明提高了效率,但又觉得这种发明与其说“是用机器战胜了人,还不如说是把人变成了机器”。福特的另一大创举是,通过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成功创造了需求和消费,也为日后美国打造消费型社会贡献了智慧。
KKR私募公司的创新特色首屈一指。成立于1976年的KKR是以收购、重整企业为主营业务的股权投资公司,尤其擅长管理层收购,其目标是“围猎”其他有潜在收购价值的公司。KKR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企业及公共养老金、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以及大学基金。在过去的30年中,KKR累计完成了146项私募投资,交易总额超过了2630亿美元,其中又以收购烟草巨头纳贝斯科最为著名。
然而,作为一家私募公司,KKR没少遭受业界尖锐的批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按照所有的存在皆合理的原则,KKR的成功其实也是企业盘活资源的写照,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促进企业发展,间接性地维护公共利益,只不过这根链条更长,转折更多。
反噬公共利益的警钟频频敲响
事物总是矛盾对立的。
在回顾公司3000年的发展史后,马格努森指出,公司并不会总是表现得那般温恭顺从,即便这些公司曾经在公共利益方面有过什么丰功伟绩。反倒是 “在历史长河中,令人发指的案例比比皆是,罄竹难书:本应为罗马共和国征税的公司最终奴役臣民,腐蚀元老院;美第奇银行篡夺行会的政治权力,并利用银行资产为其家族成员的个人野心提供资金;东印度公司在从印度到波士顿的多起全球纷争中与英国王室纷争不断;南北战争结束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通过欺诈美国政府来提高贫农的铁路费率……”
公司有时像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在“利己”的同时常常也会“利公”。如埃克森石油公司提供的廉价煤油,曾帮助那些原本买不起鲸油的普通百姓终于也可以“熬夜消费,如吃饭、喝酒、读书,还有娱乐”。但逐利本性又常常会令他们忘乎所以,贪得无厌。曾有段时间,“原罪”似乎成了初创公司难以规避的暗礁。一些成熟乃至枝繁叶茂的公司在蚕食公共利益时依旧咄咄逼人。同样以埃克森石油公司为例,马格努森不无诙谐地指出,“埃克森石油公司为反对气候变化法规所做出的大部分努力得益于匿名行业组织的庇护”。
相较于上述这样的“明枪”,马格努森认为“暗箭”更加难防。本书最后的一个案例留给了脸书。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杰出代表,马格努森虽然对这家公司的创新给予了褒奖,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脸书的算法,可能诱导消费者选择性地接受某一方面或者说是带有倾向性的信息,久而久之就可能为个人认知打下“坚实”的信息基础:你所认为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你真正应该认为的。话说起来有点拗口,事实上就是你的思维方式已经因为算法而受到了影响。很难界定企业是否存在主观恶意,但公共利益显然因为算法而受到侵蚀。
显而易见,反噬公共利益,这与公司诞生的初衷背道而驰。马格努森并不认为公司的“利己”与“利公”属性是零和博弈,所以在本书的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即从立法层面增加公司的透明度;构建有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环境;完善股份机制,让公众分享更多成果,同时强化对公司的监督;打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体系;鼓励公司像福特那样善待员工;构建符合生态保护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人类是群居社会,群居就有公共利益,就需要有公司这样的组织为公共利益服务。一个繁荣的社会,公司也必定欣欣向荣。公司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功不可没,但公司并不总是自带善良品质。从公司3000年的发展史来看,公司到底是专门“利己”,还是在发展同时积极“利公”,并不能取决于公司的高风亮节,而应根据时势发展,构建既能适应公司自身发展,又能驱使公司积极投身公共责任的机制。没有完善的机制,再良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张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