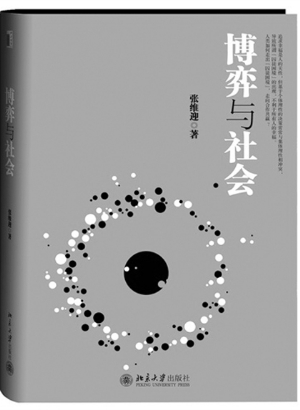|
——评张维迎《博弈与社会》
⊙潘启雯
提起理性人之间的合作,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是博弈论中所谓的“囚徒困境”:每个理性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好的行动,但最后导致对所有人不好的结果——这正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于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发明了诸如言语、文字、产权、货币、价格、公司、利润、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钟表、计算机、网络等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以求走出“囚徒困境”,不断走向合作,由此才有了人类的进步。当然,每次进步都会伴随新的“囚徒困境”。比如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更大范围合作空间,但也为坑蒙拐骗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
因而,在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他的新著《博弈与社会》正是以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法律、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大学治理等社会问题为引子,探讨了“人类如何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共赢”这个主题。
为了形象地、全方位地审视“囚徒困境”问题, 张维迎化繁为简,首先讲述了一个“智猪博弈”的故事。
话说一个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在猪圈的一头装有按钮,另一头装有食槽。在这头按一下按钮,那头的食槽会出现8单位食物。但不管是大猪还是小猪,按钮都需花2单位食物成本。如果两头猪一起按,各付2单位食物成本,然后大猪吃到6单位食物,小猪可吃到2单位食物,扣除成本后,双方净收益分别为4和0。如果大猪按、小猪不按,则小猪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可吃到3单位食物,大猪按完后跑回来还可吃到5单位食物,扣除其按按钮的2单位成本,大猪净收益也是3。如果大猪不按、小猪按,大猪可不付出任何代价吃到7单位食物,小猪则只能吃到1单位食物,扣除其2单位食物成本,则小猪的净收益为-1。
在这个“智猪博弈”中,大猪没有占优战略,大猪的最优选择依赖于小猪的选择。而对小猪来说,如果大猪按,最优选择是“不按”(3>0);如果大猪不按,最优选择仍是“不按”(0>-1)。选择“不按”是小猪的占优战略。显然,小猪在决策时并不需要假定大猪是理性的,因为无论大猪是否理性,小猪的最优决策都是“不按”;但大猪的情况不同,即使小猪是理性的,如果大猪不知道小猪是否理性,就没有办法选择。假设大猪不仅是理性的,也知道小猪是理性的,那大猪的最优选择只能是“按”。博弈结局就是:大猪“按”、小猪“不按”,各得3单位食物的净报酬。
“智猪博弈”的均衡解,在现实中有许多应用。譬如,在股份公司中,股东承担着监督经理的职能,但有大股东和小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收益很不一样。监督经理需要耗费时间搜集信息,在监督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大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好处显然多于小股东。所以,均衡结果是,大股东担当搜集信息、监督经理的责任,小股东则搭大股东的便车。股市上也是如此,“跟庄”是散户的最优选择,而庄家则必须自己搜集信息分析行情。市场中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研究开发,为新产品做广告,对大企业来说是值得的,对小企业来说则可能得不偿失。所以,大企业往往负责创新,而小企业把精力花在模仿上。
国际范围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也类似一种“智猪博弈”。在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现象,伤害所有的国家。但反恐的成本极高,所以小国没有反恐积极性,一定是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小国搭便车。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这个道理。社会改革也同样有类似的情况——同样的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另一部分大得多。此时,前一部分人比后一部分人更有改革积极性,改革往往就是由他们推动。如果改革能创造出更多的“大猪”来,改革的速度就会加快。
与“智猪博弈”故事相映成趣的是“鹰鸽博弈”,这也成为张维迎分析“囚徒困境”的有趣案例。
设想一个群体中有进攻型、温和型两类人,前者称为“鹰派”,后者称为“鸽派”。个体之间随机相遇,一对一博弈。如鹰派与鹰派相遇,两派俱伤,各得-1;如鹰派与鸽派相遇,鹰派得1,鸽派得0;如果鸽派与鸽派相遇,各得0.5。
在对比中张维迎发现,这与现实中许多组织的情况颇为相似。一个组织里既有强势的人,也有温和的人,两类人可以和平相处。但如果强势者比例过多,彼此之间相互厮杀,反倒有利于温和的人生存。反之,如果温和的人太多,强势的人就可占便宜,进而会吸引更多的强势者加入。譬如,男女交往中有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说法,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许是“坏”男人在男人中的比例很小。
“职业经理人和政府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股东和老百姓免于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也是张维迎重点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如果甲、乙都选择努力工作,各得6的支付,那是帕累托最优。但由于“囚徒困境”,每个人的占优战略都是偷懒。所以,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两个人都偷懒,结果每个人只能得2。如何解决团队生产中的偷懒问题?早在1972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就发表了《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提出了调整所有权的解决方案:使其中一人成为所有者,另一个人变成雇员,让前者监督后者。并根据后者的表现实施奖惩。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权解决了团队生产中的“囚徒困境”问题。
《博弈与社会》另一个的突出特点,是展开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的许多有趣内容和分析。信息经济学是与博弈论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专门对付“信息不对称”或“信号传递不对称”等给人们和市场带来的新问题。但其与人们所熟知“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博弈不同,张维迎以“抓小偷”为例做出了全新演绎:A在某个公共场所发现一个人正在行窃,曝光的成本是A可能受到小偷的报复,但A为了显示自己是见义勇为的人选择曝光。在A喊“抓小偷”之后,周围的人马上围上来,他们也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有些人开始殴打小偷,直至最后把小偷打死。
借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张维迎分析认为,“人们在殴打小偷的时候考虑的是个人的成本和收益(‘声誉’),而不是社会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出于传递信号的行为不一定导致社会最优的结果——即小偷有错,但罪不至死。谁该对小偷的死负责?没有人负责!作者警示人们:有时候,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被别人认为有错,自己有口难辩,就会受到严重的羞辱性惩罚,被排挤,被驱除,一生蒙受不白之冤。比如过去在农村,某个女孩子一旦被误认为性行为不检点,就会受到许多“正人君子”的指指点点,最后只好用自杀证明清白。
显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博弈往往都只能是一种“混同均衡”,而不是“分离均衡”。某人遵守社会规范并不能告诉大伙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本身就是个悖论。而张维迎把破解这个悖论的方法寄托在声誉模型和信号传递模型的结合上:在声誉模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坏人”有积极性装“好人”;在信号传递模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好人”想把自己与“坏人”区别开来。如此,在一个重复博弈的信号显示模型中,“坏人”就有积极性模仿“好人”遵守社会规范。尽管最后得到的是“混同均衡”,但两类人遵守社会规范的目的不同:“好人”遵守社会规范是为了显示自己本质上是“好人”,“坏人”遵守社会规范是显示想成为“好人”。只有一小部分极“坏”的人才不遵守社会规范。
经济学之所以能吸引众多追随者,或许正是源于经济学家对日常生活事例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就比如在张维迎笔下,博弈论不再是高深莫测的抽象理论,而成了剖析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的利器。难怪,凯恩斯早把经济学定性为“研究人类日常生活”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