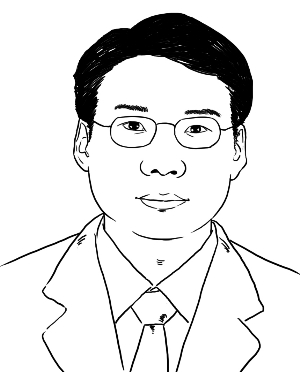|
□袁 东
原本想通过金钱与权力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国家政策”来维持甚至增强团结资源的“西方”,正逐渐失去团结资源,社会一体化力量的一个支柱正在弱化。“西方”还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值得他们标榜的几百年吗?
现代话语中的“西方”,其实相当狭小,严格说来,仅指基督教世界。而即便基督教世界,真正属于“西方核心”的也就是天主教和新教集中的地区。至于基督教第三个分支东正教所分布的地带,并非是真正的“西方”,起码不是“西方核心”。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新教伦理”的衍生品,南欧的天主教聚集区并不是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源地。即使从路德的“新教改革”算起,现代意义的“西方”也不过500年左右。在当然,这500年是“西方”苏醒、崛起并主导世界的时代。
而现在的“西方”,从19世纪起就进入了傲慢和偏见的轨道,在唯我独尊和无比优越的“中心论”持续了近200年后,那种逐步生成并迅速膨胀的自信,已蜕变为十足的自负。如果说自卑是岸上自负之树在水中的倒影,风吹水皱,那个倒影不易被人觉察,那么,岸上招摇摆舞的自负之树,却总是显目刺眼。极度的自负,已然赶走了自信。这已被“西方”的有识之士意识到。
“西方”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最大成就,即为“西方中心论”者所标榜的“现代文明”。这一文明首先从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出发,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并改造自然,服务于人类;其次是从确认并保护世俗化私人利益出发,通过广泛而自由的市场交换,促进了资本的充分运用和积累;第三是从公权与私权的明晰划分出发,通过政治权力公共化、法治化、行政化,规范和约束市场交换系统,保持社会平衡。前两者合起来,促进了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以求获取物质上的充裕;最后一点是通过“政府干预主义”建立了再分配机制,维持着民族国家的边界及其内部均衡。
简言之,“西方”带来了三种手段:金钱、权力和团结,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三种资源。经济交往完全货币化,人类正在经历着货币文化时代;权力既有对自然支配与控制,也在规范和管理社会,即行政权力;行政和市场的结合,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团结的社会一体化力量”,没有对传统价值和文化知识的继承,各个群体就无法有效整合起来,也就缺乏可以汲取的力量形成政治意志。
问题是,当代“西方”的团结资源正在趋于衰竭。对内,传统价值尤其是宗教文化,只是囿于精神领域中的边缘地带,人文主义让位于金钱与权力;社会再分配机制,正如哈贝马斯所揭示的“本质上只是在处于依附地位的就业者集团内部进行水平调节,而对特殊阶级的财产结构,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再分配则几乎没有触及。”对外,则是一味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遵循“中心与边缘”的模式,四面出击,不是团结,而是制造矛盾、冲突和分裂。
更成问题的是,金钱与权力相互交织促进,特别是权力随着金钱财富的不断扩充而肆意铺张,“国家干预主义”指导下的政府规模和触角不断扩张与深入,“社会福利国家”无不成为各政党的纲领,变为政治鼓动的号角,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也未能改变这一潮流。日常交往的生活世界,正在各种确保“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政策中逐步被侵蚀。
原本想通过金钱与权力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国家政策”来维持甚至增强团结资源的“西方”,正逐渐在失去团结资源,社会一体化力量的一个支柱正在弱化。1984年11月26日,哈贝马斯应邀在给西班牙议会所做的一场报告中,从时间意识、时代精神、历史思想、乌托邦思想、劳动社会、交往社会等在“西方”的变迁中,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哈氏认为,正是历史思想与乌托邦思想的融合,才成就了“现代的自我确证”,树立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现实期待”:“如果乌托邦这块绿州不见了,将会出现的是一块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荒漠。”当代“西方”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正是从“劳动社会的乌托邦”那里汲取了力量——将劳动从异己的决定中解放出来,变为自主活动,达到人的自我实现与幸福。
诚然,正如哈贝马斯的结论,社会福利国家已成“西方”的一种民主法治国家制度,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逆性。可是今天,“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陷入了死胡同”,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来源的“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一道走向了穷竭”。所以,哈氏无奈地总结道:“发达的资本主义既离不开社会福利国家,又无法用社会福利国家来进一步完善自身。”
如果按照布洛赫和曼海姆的定义:“‘乌托邦’是规划生活的有效手段,它扎根于历史进程当中。”那么,当“西方”的乌托邦力量已穷竭时,也就失去了筹划未来的能力,而这带来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人们只有“当下”,顾不上或看不清甚至没有“未来”。除此之外,这还带来了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新的非了然性”——“情况在客观上就那么一目了然。”
“非了然性”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问题的关键是,正如哈贝马斯的质问:西方文化是否还充满自信?“西方”还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值得他们标榜的几百年吗?若仅依据当今“西方”的自负程度,可真就不存什么“非了然性”了,有的只是带有否定答案的“了然性”。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