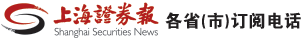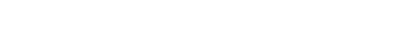如何摆脱
“停滞性紧缩”
|
全球市场近期的剧烈动荡,为全球复苏前景陡然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特别随着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价格总水平剧降,通货紧缩压力陡增。从金融流动性到经济增速,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和通胀低迷也引发了全球央行的深深忧虑。如何摆脱“停滞型增长”是摆在各国面前的特大难题。
尽管学术界对通缩的含义各有界定,但都强调一个必要条件,即物价全面持续性下跌,呈现出“停滞性紧缩”的特征。当前,包括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等多个经济板块在内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行。据摩根大通全球通胀数据,去年二季度全球通胀率为1.6%,不仅低于前年底的2%,更远低于1990年至2013年间全球11%的平均通胀水平。即便去年欧洲央行祭出了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也难以力挽狂澜,欧元区通胀率仍徘徊于临界线附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深层次矛盾突出,工业生产下行,中国降低产能、削减库存等结构性调整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需求不足,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蔓延。
现在看来,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的因素有所增加,而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上行的因素有所减少。美元货币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前提。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是美联储从过去10年的量化宽松周期开始转向紧缩周期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美元升值效应通过“进口-购进价格-PPI-CPI”的渠道影响价格总水平。美国既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入者”,也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出者”。由于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基准计价货币,美元持续升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去年,彭博全球大宗商品指数下跌25%,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低。全球油价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暴跌36%,国际原油市场遭遇重创。
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和产出缺口扩大也是导致通胀低迷,甚至通缩的重要因素。2008年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来,全球需求动能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全球工业产出以及新订单指数低迷,显示制造业复苏迟缓和低迷。此外,据WTO数据,2008年至2012年,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例由6.9%升至9.5%。金融危机肆虐三年间(2008年至2010年),全球进口总体萎缩8.4%,中国逆势增长23.3%,成为全球需求主要支撑者之一,然而随着近年中国启动“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进程,增量需求大大放缓,产出缺口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的竞争焦点直接导致了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和国际贸易先行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由2014年11月1464点跌至目前的905点,跌幅高达38%,为30年来的低位。
在美元升值周期还在进一步加大债务通缩压力。据IMF数据,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为50.95万亿美元,规模同比上升2.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负债率为108.32%,同比上升0.66个百分点,债务风险依旧困扰着发达经济体。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人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0%,升至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近200%,到2013年更达到了215%。
美元步入的新周期将增大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并推升全球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上升。据IMF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非金融类企业的海外发债规模急剧飙升,其本质大多是新兴市场大企业利用离岸子公司在离岸市场所发行的债券、跨境外币贷款来资金套利。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14年至2018年,所有新兴国家需要展期的企业债务将达1.68 万亿美元,其中约30%以美元计价。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新兴经济体债券展期成本势必显著上升,债务风险随之升温。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和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全球主要经济体步入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2008至2014年期间,叠加了美系货币国家和中国两大经济体的人口周期拐点。以15至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衡量,美系货币国家和中国在2006年至2009 年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周期峰值,欧元区和日本人口周期已于1988年至1992年见顶,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给失衡,并引发全球需求萎缩和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的7年多来实践证明,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格局已变,欲逃离通缩和流动性陷阱区域,单靠延缓美联储加息和全球央行再次启动货币宽松已难有实效。眼下,全球面临的通缩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须以结构性改革应对。寻找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切实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