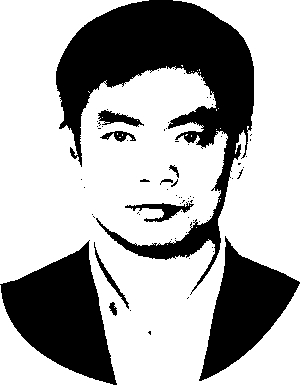|
无论是高难度的通胀预期管理,还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都迫切需要决策层将治理内外经济失衡作为今年和“十二五”期间的基础性任务来抓。
不少市场人士先前预测,为了抑制恼人的通胀势头,央行会再次启动加息这个工具,只是春节后立即启动,有点出乎意料。这次,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在上调25个基点之后分别达到了3%和6.06%。不过,即便如此,似仍赶不上还在加快的通胀脚步,目前的实际利率可能仍为负值。各方普遍预计今年还将有一到两次加息的可能。
被海外媒体称为进退两难的中国央行在驾驭货币政策方面的确有些捉襟见肘,不过这并不表明央行的专业水平与政策预见能力在原地踏步,而是央行在调控中国这个具有世界性影响且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时,面临的约束条件实在太多。假如把时光往前推30年,相信那时央行的任务不会像今天这样复杂且吃重。换句话说,在管理通胀预期方面负有最重要责任的央行,有时不得不扮演着自相矛盾的角色。尽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背后的政策逻辑,尽管中国央行比任何其他市场主体都明白扎紧货币发行篱笆的重要性,但是在执行两年多以前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需要制造天量信贷需求时,在保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发放至少7万亿元的信贷时,在面对愈来愈难以管控的商业银行放款冲动时,在去年一年的新增外汇占款就达到2.9万多亿时,在面对银行体系外一年动辄四、五万亿元的信用规模时,要控制融资总量抵御通胀来袭,除了央票、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政策工具之外,就是最具实际效力的利率调控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央行的政策困境体现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负效应。虽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深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内外收支均衡实在是难以同时实现的高难度经济目标,但在一个经济生态相对平衡的经济体里,上述经济目标也绝非无法企及。可是今日中国的现实经济状况是,日益严重的内部经济失衡尚未缓解,外部失衡趋势也未得到有效遏制。这些年来,在促进经济增长是各级各地政府第一要务的宏观背景下,对投资和出口的偏好是普遍的政策认知并得到一贯执行。其结果,中国每年创造的新增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居高难下,平均在40%至45%,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80%。而美、德、法等国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一般为10%至20%。如今中国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4亿至5亿元;而上述国家一般只需要1至2亿元。笔者估计,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中,真正有效率的比重不会超过30%。所以,欧洲经济看起来死气沉沉,但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有效经济增长却是我们难以比拟的,故一言以蔽之,在中国各地上演的如火如荼经济增长大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
在经济内部失衡加剧的同时,外部失衡也在威胁着经济的良性发展。过去十年,在入世“红利”的驱动下,沿海地区以压低劳动力成本、资源提前消耗与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出口的高速增长、巨额的外贸顺差以及经济规模的急速扩大,但这种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且寅吃卯粮的投资与生产狂热是不可能持久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当年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何等的狂飙,早在1968年,日本即跻身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产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达到大陆的一半,但是主要依靠产业结构转移以及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确保持续发展,如今,越来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以及遭遇的巨大升级瓶颈已成了横亘在我国台湾经济面前的两道高墙。
我们决不愿意看到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大陆经济核心地带的经济发展陷入今日我国台湾地区的这种状况。而从经济重要性和系统性的对比来说,日本的经济发展教训绝对值得中国镜鉴。同样,钟情于美国模式的经济学家们现在终于认识到,美国尽管可以仰仗美元本位来定期向世界辐射经济风险和转嫁经济危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框架下,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只会恶化本已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最终使世界经济由失衡走向失控,美国也不得不痛苦地疗伤。
鉴往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稳定重要性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实现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还是高难度的通胀预期管理,乃至对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极为关键的战略转型,都迫切需要决策层将治理内外经济失衡作为今年和“十二五”期间的基础性任务来抓。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正视日益严重的内外失衡引致的显性和隐性经济风险。这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尽速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之间找到均衡点,并且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另一方面,如何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进程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努力将庞大的外汇储备降至合理的线位并积极拓展外储运用渠道,也是考验决策层和政策执行者的关键性命题。当然,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理应回归到民生福祉的改善上。正如广大网民热切期待的那样,如果全国各地的GDP增长能与民众的幸福感同比例提升,如果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早日建成,那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可畏惧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