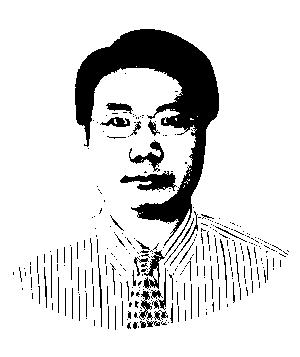|
袁 东
极少有经济学者不看重其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实用性。这没什么不好。问题只是,理论的实用性取决于能否符合现实。如果仅仅是逻辑严密,但理论体系建立的前提同现实南辕北辙,由这一体系推断出的政策主张,难免不会使各类主体误入歧途,助长而不是缓解经济生活的混乱。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为了追求永恒而陷入了“神话”的怀抱。那些学者们又忘了,孕育于神话怀抱的是诗和哲学,而不是经济学。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对时间处理的不当,或者压根儿没有考虑时间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均衡”和“失衡”概念的推崇。
尽管在几乎所有人看来,连续不断从我们手指缝里溜走的时间,都只不过是“一种生活事实”,但我最近读到的一位美国社会学者对时间的重要性,有这样的概括:“时间不仅是变化的必要方面,而且是稳定性的必要方面,因为稳定性不是别的,恰是一种意识——意识到某种事物不因周围环境甚至内部成分的变化而变化。除了变化和稳定性之外,时间还是秩序的核心。正如穆尔所说,没有时间秩序就根本不存在秩序……对当代工业化社会而言,时间是根本。工业化社会的成员不仅用时间概念来综合思维身体、自然与社会生活的种种形态,而且把时间作为全球测量、协调、管理和控制标准化的准则。”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一度受“凯恩斯革命”所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这一学说体系的假设前提是,价格机制能使市场以至经济体系由一种“均衡”瞬时转到另一种“均衡”;作为均衡的“稳态”,是经济的常态,不管是随机因素还是其他外部冲击,都只会造成对这种常态的“瞬时”偏离。上世纪70年代后,“理性预期”概念更是将人的理性绝对化:能准确预测未来。从此,“时间路径”彻底在经济分析中消失 。新古典经济学不再重视“不确定性”,似乎什么都是可量化的可计算的可测的可知的,未来是确定的,从而使这一主流学说步入了自以为然的“永恒”。
极力恢复新古典经济学主流支配地位的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物奈特,一再强调了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区别:风险只是可以概率化,从而能够通过商业保险和投资分散化予以规避的不确定性,但这仅仅是不确定性中的一部分,大部分不确定性是无法被概率化的 。他把那本代表性著作冠名为《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对不确定性的重视可见一斑。
不过,到了他的弟子和后继者那里,却将不确定性等同于概率风险。于是,在这些主流学者的理论中,市场手段可以解决一切不确定性,未来由此变得可知与确定,完全可控的“瞬时”即可代表永恒,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在他们眼里,不存在解决不了的经济问题。
可是,对一再发生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市场波动,尤其是2007年源自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的大规模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学总是难以自圆其说,日渐尴尬,以至面对围攻和诟病几无还手之力,只能无奈地将危机归咎于“失衡”。但这些声音,从一开始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成了一种自我循环式的强词夺理。
为什么?“没有时间秩序就根本没有秩序”!由于西方核心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后就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思维和行动决策的思想源泉,“均衡转换的瞬时假定”深入人心,不仅自身经济调整和社会机制建设疏于懈怠,还将这套思想以“华盛顿共识”的名目对外推销。“瞬时”假定运用的极致体现,是对前苏联开出的“休克疗法”改革处方,结果使俄罗斯成了这一思想的最大受害者。
其实,正如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的批评,经济运行从来就是不均衡的,经济向来是在非均衡中增长的,均衡只是“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思维抽象”。正因非均衡,才有企业家超额利润的获取,也才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冲动。正因非均衡,才需要经济调整,也才有以何种方式对非均衡做出调整为依据的社会体系与制度优劣的评价。但经济调整从来都不是“瞬时”的,而是有着各自的“时间路径”,是个“过程”。
正因非均衡及其调整的非瞬时,所以,变化和不确定性就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正因大部分不确定性并不是可以概率化和计算的风险,所以,未来不可能被准确预知。这意味着,信息不可能是对称的,经济生活做不到完全透明,由此,我们才称企业家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先行者,才有“风险补偿收益”之说。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过,德国历史学派是只有历史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是没有历史的经济学,而他的货币主义是历史与未来相结合的经济学。现在看来,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主流学者所推崇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未来的静态理论,货币主义学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
如果说上个世纪海德格尔对时间的重视,强调人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是为了拯救当时的哲学危机,那么,看重经济活动的“时间路径”,将时间因素充分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或许是对经济学危机的拯救。(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