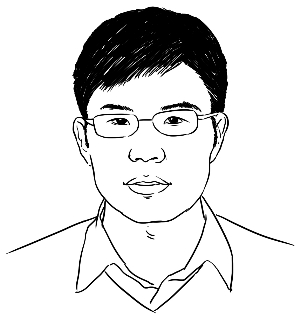|
无论是竞拍还是摇号限购,都会扭曲消费者的行为,既然治堵、排污、安全的代价不可避免,那何不另辟蹊径——完全放开限购,同时在高峰时段收取道路使用费?如此不仅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也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可谓一举多得。
为抑制汽车保有量的过快增长,减轻由此带来的严重拥堵、环境污染、交通事故频发等一系列麻烦,我国部分城市出台了形式不一的汽车限购措施。上海早在20年前就实行了新增客车额度竞拍制度,北京在2010年出台了通过摇号方式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的制度,广州、天津、杭州则同时采取竞拍与摇号的方式来控制小客车增量。
从控制汽车保有量过快增长的角度看,竞拍与摇号的效果并无差别。事实上,只要将新增汽车数额控制在消费者意愿购买的数量之下(也即实行配额制),采用任意准则(包括竞拍、摇号、排队轮购等)分配汽车都能达成限购的结果。由于购买和出售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意味着,配额制下,无论竞拍、摇号还是其他的准则,对汽车经销商和生产商的影响是一致的。
从(潜在)消费者的角度看,竞拍与限号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地方。竞拍和摇号政策都会显著改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政策出台或开始执行前,会诱发消费者提前购买甚至大规模囤积的行为;而在政策正式生效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又很可能被迫推迟。也即是说,无论是竞拍还是限购政策,都会扭曲消费者的行为,在此意义上,两者的影响是相似的。然而,在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上,竞拍和摇号政策并不相同。
摇号政策,实质上是在摇号参与者之间随机分配购车权,因此政策实施后,消费者无论近期有无切实购车需求,都会一窝蜂地去参与摇号,这就会使得每个参与者的中签率均显著降低,增加了那些真正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的购车难度。目前,北京市车牌摇号中签率已低于1%,购车难度可以想见。并且,由于一“号”难求,一旦中签,即便那些并无购车需求的摇号者,也会因车牌而购车。换言之,摇号政策一方面使得大量有切实购车需求的消费者因难以中签而迟迟无法购车,另一方面又使一部分至少暂无购车需求的人因为车牌中签而提前购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租值消散,因而是缺乏效率的。
相反,车牌竞拍政策并不会导致缺乏效率的结果。只要拍卖机制设计适宜,那些最迫切的购车者一定愿意出最高价,从而能拍到车牌号并及时购车;对于那些购车需求不太迫切、购车欲望不强的人而言,自然不愿意出太高的价格来竞拍车牌,中标的可能性就较低,也就不会出现被迫提前购车的现象。这样,消费者通过出价的方式表达购车的意愿,尽管与不出台任何政策时相比多付出了代价(不出台任何政策时车牌是免费的),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并没有浪费产生(即没有租值消散)。
那么,竞拍是不是一定就比摇号好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竞拍还有另一种负面影响:获取车牌要付出金钱的代价,这相当于在购买汽车的价格上加了一项固定的费用。假定车牌中标价格为6万元,那么这6万元就相当于固定费用,无论购买价格50万高档车还是购买价格5万的低端车,都需支付。问题在于,一个愿花6万元甚至更高价格获取车牌的消费者,通常不会购买一辆价格为5万元甚至更低的汽车。反过来看也许更好理解:购车预算在5万元或以下的消费者,不大可能为车牌付出6万元甚至更高的价格。
类似的现象并不罕见。在支付一项固定的价格后,吃自助餐时你不会只吃青菜萝卜;同样,在五星级酒店进餐,你不大可能就咸菜吃馒头;在有着相同运输费用的情况下,同类产品中售卖到外地或出口的质量一般较高;一个时间宝贵的人,好不容易得闲去听演唱会,多半会选优质座位;一个中国观众远赴美国观看NBA总决赛,也不大会选购廉价座位;如果邮局寄包裹以每箱计价,那么箱子一定会被装得满满的,而每箱的重量立刻增加;其他如宝马配名鞍等,皆可以此类推。
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超市的西瓜论只卖,消费者一定会从可选择的西瓜里面挑选个头最大的,因为个头愈大,分摊到单位重量上的西瓜价格就愈低——从而需求量也就越大。同样,如果无论优质产品还是低档产品,在价格之外均有一项固定金额要支出,那么为摊薄这项固定支出,使得单位价格更低,消费者就会倾向于选择优质产品。关于这一点,张五常教授在《科学说需求》中有完整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这里要指出的重点是,在车牌号码竞拍的条件下,由于车牌价格是购车的固定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低端车销售放缓和占比下降。并且,随着车牌价格的上涨,这种影响也会增大。如果有详细的销售数据,或可看出上海低档轿车销售量占全市轿车销售总量的比重低于北京或其他城市。再进一步,由于低档车多为自主品牌,因此车牌竞拍政策很可能在客观上抑制了自主汽车品牌的发展。
既然治堵、排污、安全的代价无可避免,那何不另辟蹊径——完全放开限购,同时收取道路使用费?放开汽车限购,有利于繁荣消费市场,提升经济活力;而在高峰时段收取道路使用费,则不仅有助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由于遵循多使用多付费、不使用不付费的原则,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可谓一举多得。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