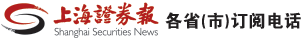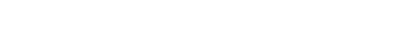机器人还不会有“普鲁斯特记忆”
|
在上周于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八届DOTA2邀请赛上,OpenAI连续输给巴西和中国队。事实证明,机器学习仍存在很大局限性,在包括游戏等太多领域,尤其那些靠情感、体验、交流驱动的服务型工作,人工智能既不是人类的对手,也无法形成取代之势。
在不同领域、数次回合的“人机大战”中,人类战队好不容易扳回一城。问题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过去几个月内,OpenAI在一款名为“DOTA2”的战略电子竞技游戏中接连战胜人类业余选手队和职业玩家队,昭示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在游戏环境中,需要考验人工智能的即时决策力、判断力和相互配合力,要求机器复杂算法和深度学习的能力更为出众。OpenAI在比赛中的反应时间从0.080秒被调整到0.2秒,更接近人类水平(以尽可能实现公平竞争)。对比AlphaGo曾在围棋对弈中先后战胜李世石、柯洁等数十位世界级棋手,OpenAI的获胜代表着人工智能在宏观、整体决策层面的表现迈入一个新阶段。
而当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 CTO(首席技术官)格雷格·布罗克曼带着全新一代OpenAI Five如期而至,想在DOTA2电竞中再次挑战人类时,却遭遇到阻击并败下阵来。就在上周于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八届DOTA2邀请赛上,OpenAI连续输给巴西和中国队。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在《机器之心》中写道:“2019年,通过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我们可以观看3D动态影像、进行3D可视通话、进入虚拟环境。家用机器人进入普通家庭,可以做清洁工作或者其他家务。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一般都有机器智能监控,以防出现人类之间的暴力。计算机化的健康检测器广泛使用,它内置在手表、首饰及衣服中,可以诊断急性和慢性健康状况。”这一年是“即将到来的技术变革的一年”。而10年后,人类和机器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库兹韦尔在为机器描绘富有“雄心”和“野心”之举的路径图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它们的“短板”?
2016年以《北京折叠》获雨果奖的郝景芳在小说集《人之彼岸》中揭示了这么一条:人工智能再发达,但在其头上将盘旋“三朵小乌云”:综合认知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和自我决定的能力。而OpenAI软件工程师的一番话或许可视为对郝景芳观点的批注:“如果人工智能在比赛中遇见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情况,很难立即调整。同时,在训练过程中,机器人在判断采取何种行动时,最多会提前14分钟。没有任何机制能让机器人部署超过14分钟的长期战略。人工智能这一缺陷,在(与巴西队、中国队的)两场比赛中暴露无遗。”比起国际象棋(1996年IBM开发的“深蓝”成为第一个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较量并赢得比赛的电脑系统)或围棋,电子竞技游戏要求人工智能在团队协同作战、布局长期战略和制定复杂策略上拥有更高的能力(“算法”)。事实证明,机器学习仍存在很大局限性,在包括游戏等太多领域,人工智能既不是人类的对手,也无法形成取代之势。
自人工智能出现以来,对它究竟会不会抢夺人类的饭碗以及何时全面“夺权”的争论就未停歇过。有“技术超验主义者”之称的凯文·凯利就认为,“这不是一场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竞赛,而是一场机器人参与的竞赛。如果和机器人比赛,我们必输无疑。”最近,他貌似修正了说法——智慧有不同维度,好比一支交响乐团,不同的乐器能弹奏出不同的声音,所以,人类和人工的智慧分属不同维度,后者也不是最聪明的。他认为“未来,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既不是人,也不是AI,而是‘人头马’”。这当然是个比喻,“人头马身”指的是高智商人群加上人工智能技术。无疑,凯利奉行的是“智能增强”路线。
上世纪60年代,马文·明斯基和约翰·麦卡锡自“达特茅斯会议”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世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建造出从外形到功能都与人类相似的机器人。然而,就在距这个实验室的三英里外的另一个由人机交互先锋、“鼠标之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设立的实验室,则从事智能增强研究。恩格尔巴特认为智能机器人应辅助人类,并致力于建造出能延伸拓展人类能力的机器人。由此,人工智能应用分裂出两个观念派系,一方主张要将人“排除在外”,一方则要“为人所用”。
目前看来,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威胁论”的声音显然更有市场。赫拉利在其现象级图书《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更是语出惊人,认为在“数据霸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研发进步与广泛应用,终将使许多人因无法比机器更适应迭代创新和高强度的环境从而丢掉工作。
赫拉利的警告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就在“人机大战”中人类获胜的消息传来之际,有一本完全借助算法翻译,后期经由人工审校的外版图书《极简区块链》出版了。它的话题性和特殊性完全在于“译者”——网易有道AI。据称,这本20余万字的作品,输入、翻译过程只耗时不到半分钟。不过,网易公司代表也承认,当前的自动翻译技术,只适合以事实陈述、数据罗列为主的内容,不包含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和精致叙事。如按严复的翻译“三难原则”来审视,这部号称“全球首本人工智能翻译图书”,只能说但求有“信”,别奢望“达”“雅”了。
凯文·凯利说过,“让机器人代替我们从事现在的工作,让我们在它们的帮助下去构想有意义的新工作吧。”他的想法同样不乏支持者。美国知名科技作家、硅谷创业家杰瑞·卡普兰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共生下财富、工作与思维的大未来》也直言,那些诸如靠情感、体验、交流驱动的服务型工作就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且,技术发展在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低端工种之余,也在创造新工作岗位。
所以,在机器人还不至于凭借“普鲁斯特记忆”写出类似《追忆似水年华》的作品来,人类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呢?即便要有所警觉,也得即刻审视自己是否过着诗意的日子、做着有意义的事。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知名互联网观察者)